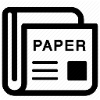《春夜十话》:一个东方心灵对数学的领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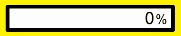
数学是逻辑性的学问吗?许多数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著名日本数学家小平邦彦认为,理解数学相当于“观察“数学现象:“观察”不是用眼睛“看”,而是通过一定感觉形成感知,是一种不同于逻辑推理的纯粹感觉,这种感觉几乎接近于视觉。他的这个观点,与另一位日本数学家冈洁的观点相互呼应。
冈洁是出生于20世纪初的日本数学家。他的多复变函数研究为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基础性贡献,深受20世纪大数学家西格尔(C.L.Siegel)、韦伊(A. Weil)和嘉当(H.Cartan)推崇。他的这些工作大都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间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
冈洁
冈洁去世40年后,他1963年所著的随笔集《春夜十话》有了中译版。这本书当年在日本出版后曾对几代日本人影响至深。它的另一个标题,《数学与情绪》,似一束思维之光,旨在照亮理解数学的另一处角落。
点击图片,一键购买《春夜十话》
这本数学家所写之书到处是随思绪漂浮和跳跃的随想,并非一本严谨的自传。关于冈洁生活只言片语的一些片段零星散布在他对数学与文化的风格自由的随笔感悟中,如一些破碎玻璃的颗粒,偶尔折射出冈洁生活时代的一小块图景。我们可以随处拾起一点碎片:在他上高中时,爱因斯坦曾到访日本,相对论在日本风靡一时,许多日本学生都报考了理科;20世纪20、30年代,日本的数学水平还远远落后于欧美,像他这样的青年数学家大都去德国或法国留学。
从法国回到日本后,他全身心投入数学研究,放弃了广岛大学的教职,卖掉房屋和田地,带妻儿回到乡下,以种植芋头为生。1937年,靠变卖家产生活不久,侵华战争爆发使得日本国内开始吃紧。战争的阴霾笼罩日本,他在乡下的房屋被征用为军用道路,一家人不得不租屋在山麓下居住。贫穷和饥饿成为游荡于他生活中挥之不去的幽灵,当时的窘况,是“除墓石外,全典卖光了”,“故乡里,无屋,只吹秋风”。日本战败后,他的生活也撑不下去,没有粮食,不得不去找工作,成为京都大学教授。
在艰苦落魄的乱世中,冈洁全身心沉浸在数学中,体会到的竟是一连串发现带来的喜悦,有些不可思议。那段战争岁月里,他体会到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乐”的境界。孔子曾说自己尚未能达到“乐”的境界,仅止步于“好”。冈洁则认为,自己能进入到“乐”的境界,与学问自身在不断进化有很大关系,“孔子时期的古代,学问缺少知性的自主性,所以孔子与学问做伴的愿望还只能停留在梦想中”。每当冈洁在数学上有了新发现,他就能体验到极大喜悦,“像阿基米德发现浮力时从浴缸一跃而出,赤身裸体跑回家的狂喜”;也像“打算出门捉蝴蝶,推门就发现树枝上停着漂亮蝴蝶时的心情“。他只顾思考数学问题,至于是否要写成论文,已全然不在乎。
我们通常认为,做数学靠的是大脑,但冈洁认为,情绪才是关键。他感到处于数学研究的状态中时,“如果交感神经系统活动起主要作用,会思绪不畅,寸步难移;而副交感神经系统活动起主要作用时,反倒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助,只是肠胃蠕动增强,容易出现腹泻症状”。他认为,副交感神经系统对于人主动兴奋地沉浸在某个状态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图 | 摄图网
进入20世纪的数学带给数学家的是一种与过去全然不同的体验。比如,三次方程的解法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数学家而言,是一道不知何时才能解开的难题。整整几代数学家穷尽一生钻研它的解法,最后才由一位叫塔尔塔利亚的人解了出来,这个过程历时两百多年。然而,当冈洁想自己探索三次方程的解法时,他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找到了与前人不同的解法,“虽不及前人巧妙,但也成功另辟蹊径”。他思考其原因,认为是人对数学的和谐感在四百年发展过程中变得更加深厚的缘故——和谐感的增强改变了现代人对“可能性“的选择方式,因而他才能在短时间内破解三次方程的解法。他猜想,现代人的和谐感与古代人的和谐感不在同一级别,”和谐感每提升一级,解决问题的速度可飞升几十倍,而如今数学的和谐感较塔尔塔利亚时代应擢升了三级”。
然而,在冈洁生活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了。在冈洁看来,20世纪之所以极端与破碎,其原因正是我们过度发展了科学,而失去了数学本质的内在和谐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高校数量不断增多,数学论文数量不断攀升,但他看到,“那些论文就如废纸,言之无物,渴望探知数学本质的人越来越少”。如今,机器已可取代和超越人类完成极为复杂的计算,甚至能代替人类从事理论性研究;那么,数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冈洁认为,它的存在是机器根本无法替代的,“晓以人类和谐的精神”,——人性的“夜色愈深,数学愈加重要”。
不过,二战后,现代数学的图景也变得更加严峻。从二战爆发前的五六年开始,数学主流已趋于“抽象化”:即舍弃内容上的细节,保留事物的基本属性。这一变化在战后更为显著。冈洁写道:“若以风景作比,战后数学世界就像严冬旷野,天朗气清,寒风呼啸,虽风景尚佳,但非宜居之所”。
从法国留学回日本后,冈洁决定专攻多复变函数论。1934年,德国数学H.贝恩克和P.图仑合著的《多复变分析函数论》在德国出版。冈洁研读之后,已能清晰展望研究领域的全貌,也对未能解决的三个中心问题了然于心。1935年,在开始研究中心问题两个月后,他看到三个中心问题“逐渐显露的真身“,”仿佛形成了一座连绵的山脉呈现在我眼前“。经过三个月研究毫无进展和昏昏欲睡的停滞状态,在一次前往北海道在朋友家度假时,他的思绪突然趋向一个方向,研究内容变得清晰可见,解法的浮现不过是在须臾之间。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酣畅淋漓的快乐。此后十年间,他一共发表了五篇论文,每两年发表一篇,都是受此启发而完成的。
冈洁的第一篇至第五篇论文,都属于函数论。从第六篇开始,则属于解析学。在《给昭和年间的遗书》里,他写道,1947年5月,他参加光明教法会五天,每天念一个小时经,回家后作数学研究。这时候,他的“心之眼”变得非常清晰。他留意到之前从未留意到的一次方程形式解的局部存在性问题,很快就用两页证出存在性来,要解的问题借此完全得到解决。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第七篇论文,《关于若干算术概念》。其中,他从不定域ideal导出几个新的基本概念,触及了数学的本质。
1948年,这篇论文以手稿的形式交付给即将赴美的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他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再经由角谷静夫、外尔交到嘉当手里,最终在巴黎出版。接着,他在1951年发表了艰深的第八篇论文《基本化的辅题》。1953年,第九篇论文《无内分歧点的有限区域》发表;1962年,第十篇论文《生成凸型区域的一个新方法》发表。他的第十篇论文以法语写成;他描述,这个过程是他“安静地用法语将内在的日本式情绪写成论文”。如果说前五篇论文是受西方严格数学思维训练的灵感式产物,冈洁认为,自己的后五篇论文是“日本式情操的产物”。
冈洁与日本之外的数学世界产生交集,和亨利·嘉当有莫大关系。亨利·嘉当是法国大数学家,也是布尔巴基学派的关键人物。大战结束后,他开办的嘉当讨论班历经16年,到1964年结束,对法国数学乃至世界数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多复变函数从古典时期向现代时期转折的过程中,他组织的三次讨论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冈洁的另一本著作《紫之火花》一书中,他写道,他对数学家亨利·嘉当感到“特别亲切”,初见就像与他已认识和相伴了三十年一样。嘉当初次看到冈洁的论文,则评价说,“冈洁论文中所说的都正确,但是那种形式还不能算是数学”。嘉当在1951年至1952年的数学研讨会中以“多复变解析函数论”为讨论题目,把冈洁的研究整理成一个体系,与和冈洁原来的论文形式已完全不同。
日本数学家小平邦彦曾引述夏目漱石在《梦十夜》中对运庆雕刻金刚手菩萨像的描述,来表达他对数学本质的感受。“运庆在金刚手菩萨的粗眉上端一寸处横向凿刻,手中的凿刀忽而竖立,转而自上而下凿去。凿刀被敲入坚硬的木头中,厚厚的木屑应声飞落,再仔细一看,金刚手菩萨怒意盈盈的鼻翼轮廓已清晰呈现。运庆的运刀方式无拘无束,雕琢过程丝毫没有任何迟疑。那不是凿刻出的眉毛、鼻子,而是眉毛、鼻子本来就埋藏在木头中,他只是用锤子、凿子将其呈现出来,就像从泥土中挖出石头一样,不会出现偏差“。冈洁对数学的描述也有这种日本式韵味。
晚年,冈洁写文章著书,发表对社会的感言,希望把日本从浮夸的现实境况拉回到过去的纯朴状态。他与胡兰成有了深交,向胡兰成学习中国哲学。日本数学家横山贤二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冈洁从西方的数学、科学和哲学思想,逐渐走向东洋的“解脱”,朝着“使事物精简的方向穷追不舍思考”,转向了佛教,进而转向神道。不过,据胡兰成的记述,冈洁“几乎不参谒佛事,很少参拜神社,几乎不见佛僧和神官。不慎说到古传秘传,就会发怒”。随着年事渐长,冈洁逐渐远离大众,回绝所有演讲,活进了越来越浓厚的孤独色彩中。1978年3月,冈洁因心脏衰弱去世。去世前他常对亲近的人说,他的数学活着时来不及做完,他要好好做准备,以便走进另一个世界后可以继续做下去。
冈洁和他那一代经历过二十世纪数次战争、目睹过历史破碎与极端的数学家一样,命运都曾多舛起伏。诸行无常,他们却反而在乱世中抱定生命的信念,希冀将其融入数学的永恒中。数学在冈洁看来,就如芥川龙之介所言的“永恒之影”,是真善美的理想,与我们的世界存在着联系,并能让我们获得实在感,却不属于理性世界。至于研究数学有何用处,历尽沧桑的冈洁轻盈地写道:“紫花地丁只需如紫花地丁般开花即可,这对春日的田野有无影响、有何影响,紫花地丁自己也不知”。
点击图片,一键购买《春夜十话》
大家都在看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
点击图片,一键下单
【春夜十话】
▼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周刊书店,购买更多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