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版权征文 | 逃离与规制:人工智能模仿人声的法律定性 ( 下篇 )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独立研究思考的成果,旨在促进学术交流,不代表作者单位及本公众号的立场和观点。
三、反面视角
是否侵犯被模仿人的权利
任何一种新事物或新商业模式的出现都会冲击现有的利益秩序,对新事物作出是否具有非法性的判断应当依据是否符合法律的目标价值以及是否促进整体社会福利的提升。目前探讨人工智能模仿人声的文献资料尚不丰富,虽然没有现成的理据,支持人工智能模仿人声不侵犯被模仿人权利的理由应该可能主要有以下几种:
1.人工智能仅仅是模仿了人声,但并不是真人声音的直接利用,并没有利用人格要素。只有综合肖像、声音等要素才能明确指向某人,仅仅靠声音难以实现对人的准确指向;
2.商品化权分为真实人物的商品化权和虚拟人物的商品化权。有学者基于此,区分了形象权与商品化权,“形象权是指自然人对其形象价值享有的权利,商品化权则不包含自然人形象价值权利;仅指自然人形象以外的作品名称、虚拟角色名称等的商品化权”。[10]按照我国司法中目前的逻辑,所有有关真人身份的商品化权,仍最好留在人格权领域予以解决。[11]解决真实人物的商品化权应当适用人格权理论,不能适用商标法上的混淆逻辑。[12]
3.人工智能模仿人声构成对被模仿者声音的合理使用,产生了新的事物、新艺术产品。但本文认为人工智能模仿声音侵犯了被模仿人的人格商品化权。
(一)会造成人格利益的减损
某些人格权尤其是标表性的人格权本身具有一定的可利用价值,人格权之外的特定人格利益,如声音、特定人体动作等也都具有利用的可能性。[13]温世扬教授认为人格符号具有外在性、可支配性、可商业利用性[14],正是这三个特点致使人格符号具有较强的财产属性。
在当今的流量时代,具有较高社会影响力的人的声音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人的声音会引起大众或粉丝的喜爱,如果将这种喜爱通过声音转移到其他物品上,则人们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也会将喜爱投射到富含声音的物品上,进而特定人的声音就会产生经济价值。而声音虽然属于人格因素,但是这些人格因素能够与人身相分离已经被民法学者广泛认可。基于人格因素外在性和可分离性,人们可以利用其人格因素实现经济价值,也可以将这些人格因素授权他人使用。
因为声音作为人格因素,蕴含着较强的经济价值,这部分权利无论是采用人格权模式还是采用商品化权的模式[15]进行保护,该权利均有积极权能和消极权能。积极权能表现在,其可以自己使用或授权他人进行商业使用。消极权能表现在当其人格利益受到侵犯时,可以行使禁止权和求偿权。因为权利人享有排除他人擅自将自己的各类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化利用的权利。[16]
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贝特·米德勒”案中认定了特定人的声音可以作为形象权的保护对象。贝特·米德勒是美国的著名歌手,某广告公司邀请其录制广告歌曲,被米德勒拒绝后,广告公司聘请了德勒的前伴唱歌手录制广告歌曲,并要求该伴唱歌手尽量模仿米德勒的声音。伴唱歌手基于对米德勒声音特点的熟悉,演唱的歌曲使听众都误以为是米德勒本人所唱,于是米德勒对该公司提起了诉讼。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当一个专业歌手的独特声音被广为知晓,他人故意模仿该声音以销售产品时,销售者就侵占了本不属于他的东西,在加利福尼亚构成侵权行为”。[17] 因此人工智能模仿他人声音,如果没有经过授权,就会造成被模仿人经济利益的减损。
(二)会造成被模仿人对其声音符号的失控
人的声音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具有指向关系。人的声音,如同面孔一样,具有可区别性与个性,人类的声音是表明身份的最易感受的方式。[18]在符号学理论中,人的声音作为一种符号可以积累人的社会声誉、承载人的综合社会评价。姓名、肖像、声音等人格要素能够吸收人格价值和形象价值而被赋予独特的第二含义,即不同于其自然属性的具有标志意义的符号意义,[19]这些符号能够准确的指向具体的人,并能够实现人与人的区分。因此声音与人具有对应关系。
有学者将人的人格要素可以分为三类,肖像、声音等生理性人格要素,也包括荣誉、名誉等社会性人格要素,另外,还包括人的情感、意志、品格等主观性要素。[20]生理性人格要素与社会性人格要素、主观性要素相连接,人工智能在模仿声音的过程中,其实质是通过声音这一生理性要素调取了被模仿者背后的社会性要素和主观性要素。根据上文分析,人工智能模仿人声具有永久性,声音使用的永久性很容易导致被模仿人失去对自己声音的控制。对声音失去控制,就会导致对社会评价、甚至情感意志等要素失去控制。被模仿人的声音很有可能被用在不雅的文本中,造成其社会声誉的降低和贬损。因此人工智能模仿声音如果没有经过被模仿人的授权,会构成侵权。当然,在这里我们仍需要分析人工智能模仿声音是否属于合理使用。
(三)人工智能模仿声音不属于合理使用
学者认为,在没有恶意的情况下,重复使用他人的商品化权人格类载体,只要不导致混淆,就是合理使用。[21]因为有价值被模仿的声音绝大部分均为名人的声音,名人基于其公共性,其权利就应当受到相应的限制。但是本文不赞同这种观点,一方面,名人的声音蕴含着更大的经济利益,更需要得到保护,而不是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即便没有主观恶意,只要利用或模仿了名人的声音,就会在客观上造成其经济利益的减损,这种减损是一种潜在的损害。我们在考虑其经济利益的损害时,不仅要考虑现实的损害,也要考虑潜在的损害。
美国合理使用的四个衡量因素为:使用的目的和性质;作品的性质;使用部分占原著作权作品的量和实质程度;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22]但四要素法主要用来判断对作品的使用是否构成合理使用,而人工智能模仿声音并不是对作品的使用,也不是对被模仿人表演的使用,而是对声音具有一定转换性的使用,最终用高度相似的声音再现一部新的作品。
那么人工智能模仿人声构成对声音的转换性使用吗?本文认为不构成对声音的转换性使用。所谓“转换性使用”,是指对原作的使用并非为了单纯地再现原作本身的文学艺术价值或实现其内在功能或目的,而是通过增加新的美学内容、新的视角、新的理念或通过其他方式,使原作在被使用过程中具有了新的价值、功能或性质。[23]转换性使用是美国在camphbell案中被确定的,被告乐队使用了原歌曲基本旋律和少数歌曲,但又重新填词,对原歌曲进行嘲弄,并产生了与原歌曲完全不同的效果。
模仿讽刺作品之所以具有正当性,一是因为批评嘲讽属于言论自由,著作权不能限制言论自由,二是因为在转换性使用的时候,作者对原作品的使用,不再是单纯的再现原作品,而是通过引用产生新的价值和新的表达,这有利于文化市场的繁荣。但是人工智能模仿人声,并不符合转换性使用,一方面,模仿人声属于传播领域,而转换性使用属于创作领域,两者的适用规则并不相通。另一方面,模仿人声进行演唱,虽然产生了新的歌曲再现,但是听众选择听模仿的人声,并非单纯为了听歌曲内容,而是基于模仿的人声与自己喜欢的人声之间高度相似。人声背后的人格因素仍然在发挥作用,因此人工智能合成人声不构成转换型使用。
通过人工智能合成人声为盲人朗读或演唱作品,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本文认为这种不构成合理使用。虽然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构成合理使用,但这仅适用于对作品的使用,而不是对声音的模仿。在完全可以使用普通合成人声的情况下,却模仿特定人的人声构成侵权。
将人工智能合成的人声进行再处理,如加快节奏,产生了滑稽讽刺效果,是否属于滑稽模仿?本文认为,这种情况不属于滑稽模仿。因为滑稽效果不仅仅是节奏的变化产生的,而是由被模仿人的人格要素、作品要素、改编要素等综合发挥的作用。
随机合成的声音很像某位名人,是否需要该名人授权?尽管不是合成的人声不是通过对该名人声音样本的采集,而是随机的毫无目的性合成的,但如果合成人声与真人声音高度相似,容易引起混淆,仍然侵犯了该名人人格利益。一方面,对人格权商品化的保护可以借用商标法中的混淆逻辑,另一方面,人格要素对应的权利属于绝对权,认定侵权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有过错,基于巧合仍构成侵权。
人工智能模仿人声者是否有向公众说明声音并非真声的义务。经过被模仿人授权后,模仿人声并不会造成对公众情感的欺骗,因为模仿的目的就是要借用被模仿人的人格利益,经过授权后无需向公众披露。
是否只有名人可以对人工智能模仿其声音主张权利?有学者认为,任何人都有将自己的人格表征加以商业化利用的机会,不应将权利的实现与权利的享有混为一谈。[24]还有学者认为该原理只属于名人。若该真人不知名,或知名度不够,则该人就不能成为商品化权的主体。[25]本文认为只有名人可以主张权利,因为名人的声音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和较大的经济价值,普通人的声音不具有这两个特征,即便人工智能随机合成的声音与某位普通人的声音很相似,因为该普通人不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不会引发混淆,其人格因素在作品再现过程中也并未发生实际作用。
四、正面视角
经授权后的人工智能模仿人声是否构成表演
既然人工智能模仿人声需要授权,那么经过授权后的人工智能模仿人声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演?该问题在本质上与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构成作品基本相同,本文在此不做过多探讨。经授权后的人工智能模仿人声是否构成表演,也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逻辑困境:一是主体客体不能互换,著作权法上要求表演者必须是人;二是人工智能模仿人声进行表演并没有体现出对作品的理解、感情和个性。
本文认为经授权后的人工智能模仿人声可以构成表演,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首先,虽然有学者主张之所以不能脱离人来单独给予机器以著作权主体地位,也不能将独创性标准调整为人工智能独立完成的结果,还是因为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不可互换的私法基本原理。[26]但这是在弱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规则,在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具有很强的神经学习能力和自主意识能力,这将对传统哲学上对主体客体的认知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而且有学者主张人工智能具有独立自主的行为能力,有资格享有法律权利并承担责任义务,人工智能应当具有法律人格。[27]当然这种法律人格是一种有限的法律人格,应该受到人类的严格监管。然而现实的例证是在2017年10月26日,机器人索菲亚被沙特阿拉伯授予了该国的公民身份。[28]
其次,虽然有学者主张迄今为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都是应用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不能体现创作者独特的个性,并不能被认定为作品。[29]但在客观上,人工智能模仿人声进行表演,已经已经具备了表演的艺术表现力。从受众的角度[30],已经可以给听众带来艺术上的享受。因此吴汉东教授主张,人工智能生成之内容,只要由机器人独立完成,即构成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至于其用途、价值和社会评价则在所不问。[31]
第三,从法律政策的角度考虑,人工智能模仿人声能够满足市场的实际需求,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文艺的繁荣。在流量社会,人们更希望欣赏到自己喜欢的名人表演更多的作品,但名人限于时间精力不能产出更多的表演。还有一些名人已经故去,靠真声无法再进行表演。这些都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模仿人声实现,但需要通过大量的成本投入才能完成。人工智能模仿人声表演作品,具有较大的市场价值,如果不对其进行保护,让其进入公有领域,则没有人愿意为人工智能模仿人声进行投资。基于法律政策的考量,人工智能模仿人声能够促进知识的传播和文艺的繁荣,在整体上增加民众的社会福利。
五、结语
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冲击现有的利益秩序和理论框架。著作权法受科技的影响最大,每次传播技术的变革总会导致著作权制度发动深刻变动。因此著作权法被动回应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常态。而人工智能会对社会产生革命性影响,著作权法也应该顺应时代洪流,积极进行理论创新,以实现传统理论与时代精神的融合。认可人工智能模仿人声构成表演将从更大程度上实现人格利益与人身的分离,有利于人格商品化权中经济利益的充分发挥。
注释:
[10]蒋利玮:《论商品化权的非正当性》,《知识产权》2017年第3期。
[11]刘丽娟:《我国司法如何确认商品化权》,《电子知识产权》2017年第10期。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第2款规定“对于著作权保护期限内的作品,如果作品名称、作品中的角色名称等具有较高知名度,将其作为商标使用在相关商品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其经过权利人的许可或者与权利人存在特定联系,当事人以此主张构成在先权益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有学者认为,该条体现了《规定》对商品化权益的保护以“混淆可能性”为构成要件,采用的依然是商标权保护的逻辑判断。杜颖、赵乃馨:《缓行中的商品化权保护——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第2款的解读》,《法律适用》2017年第17期。
[13]参见王利明:《论人格权商品化》,《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14]参见温世扬:《析“人格权商品化”’与“人格商品化权”》,《法学论坛》2013年第5期。
[15]目前学界就真实人物应当采取何种保护模式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采用人格权保护模式,虽然真实人物的人格符号所包含的财产利益与传统的人格权理论相矛盾,但是这种冲突可以通过人格权理论的革新而消除,且这种利益在本质仍然是人格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采用商品化权的保护模式,一方面,这种利益属于财产权的范畴,传统的人格权范畴通过扩张也无法容纳,另一方面,商品化权已经成为与人格权相并列的一种权利。
[16]杨立新、林旭霞:《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及其民法保护》,《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7] See Midler v. Ford Motor Co., 849 F.2d 460, 463 (9th Cir. 1988).
[18]董炳和:《论形象权》,《法律科学》1998年第4期。
[19]谢晓尧:《商品化权:人格符号的利益扩张与衡平》,《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
[20]王坤:《人格符号财产权制度的建构及其法律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21]杜文聪:《论商品化权的行使及其限制》,《河北法学》2011年第12期。
[22] 17 U.S.C.A.§107.
[23]王迁:《论认定“模仿讽刺作品”构成“合理使用”的法律规则———兼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涉及的著作权问题》,《科技与法律》2006年第1期。
[24]姚辉:《关于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若干问题》,《法学论坛》2011年第6期。
[25]汪新蓉:《商品化权小议》,《科技与法律》2001年第2期。
[26]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知识产权》2017年第3期。
[27]袁曾:《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审视》,《东方法学》2017年第5期。
[28]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4%A2%E8%8F%B2%E4%BA%9A/19464945?fr=aladdin,2018年3月1日访问。
[29]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30]梁志文教授,主张从受众角度出发,构建以人类读者(受众)为基础,而不是以人类作者、发明人为中心的版权法和专利法理论,即可解决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地位问题。知识产权法律在理念上从人类创作中心转向为人类受众为中心,并不需要法律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参见梁志文:《论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保护》,《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31]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作者系天津市高级人法院知识产权庭助理审判员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博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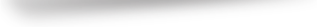
往期文章推荐
Baidu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百度公共政策研究院专注互联网行业政策法律规制,致力于从政策法律角度记录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沟通交流关于互联网政策法律问题的观点和资讯。
微信号:InternetPolicyReview
投稿合作:PPR@baid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