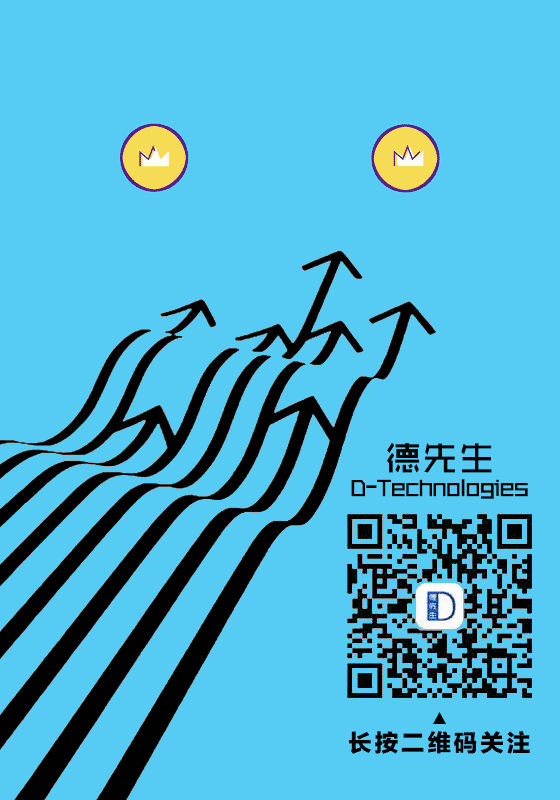诗人数学家蔡天新忆《我的大学》:除了学习知识,“人生”这一课亦不能缺

定义蔡天新似乎比较难,他是数学家,也是诗人,他在浙江大学主讲的 《数学传奇》课程入选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他在全世界十多个国家的数十座城市举办过诗歌会,他的诗歌集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他在浙江大学的学生中备受追捧。他曾经说过“文学和数学一样,都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产物”,而他的两大爱好文学和旅行,则“提升了我的数学眼界和想象力”。
大学究竟该如果度过?理想中的大学生涯是什么样的?他特地为学生写了《我的大学》。日前,这位曾经的少年大学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他对大学教育的看法。
考入山东大学数学系那年,蔡天新15岁。那是1978年,这位少年大学生赶上了好时光,青春年华与改革开放同行,亲身感受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去40年中所呈现的加速度。
如今在浙江大学数学学院任教的蔡天新出版了新作《我的大学》。在书中,蔡天新不仅回忆了自己的求学往事,也同时呈现了40年前参加高考的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大学时代往往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甚至是在我们弥留之际依然能够记得的。那个年代的学习生活环境属于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是比较独特的一部分。”
因为“追星”选择了山大少年班,五六百页厚的数学习题集爱不释手
蔡天新是1978级的大学生。据统计,1977年恢复高考后,77级和78级的高考录取率仅4.9%和6.6%。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有过如此惊心动魄升学体验的一代人,对于考大学和读大学的记忆异样深刻。
1978年的那个秋天,浙江台州黄岩县的15岁少年蔡天新来到了济南。那个年代,山东大学以文史哲见长,而蔡天新铁了心报考山大,则是因为“追星”。“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写到的人物里,陈景润和王元都在中国科学院,只有潘承洞在山东大学。后来我果然做了他的研究生。”蔡天新以高分考入山东大学,还成为“少年班”的一员。
蔡天新印象中的大学生活是“每当夜晚来临,我们几乎都在教室里,做作业、预习或看课外书,一直要到十点半熄灯才回寝室。”虽然现在看来,当时大学的设备都很简陋,但在蔡天新记忆中,大学的环境却很舒适。
那时没有很多社团和学生活动,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学生活的主旋律就是学习。抄作业或者不认真考试,那是不存在的,几乎所有同学的全部生活就是安安静静地学习。“晚自习时,我们先做作业,学习好的同学会帮助其他同学,特别是那几位已经做了父母的还有家事牵挂的同学。等我们完成作业后,学习比较好的同学会看参考书,其中就有《吉米多维奇习题集》。”
当时少有英语教材译成中文,所以蔡天新对这本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吉米多维奇习题集》爱不释手。这本习题集有五六百页厚、收入了四千多道数学分析习题,内容丰富、由浅及深,内容涉及函数与极限、单变量函数的微分学、不定积分和定积分、多变量函数的微分学等等,几乎囊括了数学分析的全部内容。因此,他和同学们几乎人手一册,“尤其是准备考研的同学,每天都要捧着它”。
蔡天新所在的山东大学少年班人才辈出,不乏“神童”级别的风云人物,而他所在的数学领域,更是神童的“高频出现区”,但蔡天新仍保持了足够的理智,表示在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纯粹由少年组成的团体容易出问题,而如果不同年龄的人在一起就可以取长补短。这方面,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学校有着较为成功的例子。”在他看来,除了学习知识,“人生”这一课亦不能缺失。
因为数学和诗歌一样“美”,所以坚决不改行
大学的数学专业在近年来经历了一个有趣的转向。数学曾经被认为是基础专业,也是较冷门的专业。而今,由于数学专业毕业生在升学、就业方面有明显优势,很多名校数学系都成了考分最高的专业。
蔡天新的同学,包括在大学期间被选拔参加“小班”“小小班”,数论训练的同学后来都在专业上转向。而蔡天新本人,则从追随我国知名数学家潘承洞教授开始,至今初心不改,专注于数论领域研究。
当被问及坚持的原因时,蔡天新给出的答案却出乎意料。“我们那个时候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我自己坚持数论研究,是因为它的美感,这与我喜欢写诗、写随笔和摄影的原因一样。”
除了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还有一个身份:诗人。他对文学以及艺术的热爱,也始自大学。
蔡天新回忆,他的第一篇随笔《数学与艺术》,是因当时系里的报纸《青年数学家》主编刘利民老师约稿。他说,语文由作为工具的语言和作为艺术的文学组成,同样,数学也由作为工具的应用数学和被数学家视作艺术的纯粹数学组成,因此两者是同构的。“之后,这篇文章又投给《山东大学报》的增刊《稚虬》,变成了铅字,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自此,我也开始更多涉足于随笔写作。”
蔡天新说,大学就是自我探索的过程,无论数学世界还是人文世界,探索的过程与获得的成果都是“美”本身。
“从大四开始,教室里自修的同学逐渐减少,而我则忙于准备春节后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常去东边新盖的教学楼看书,那时还没有随身听,我会带一台袖珍收音机。”蔡天新记得,“有一天中午,《八音盒》节目播放了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舒曼的《童年情景》、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这几段闻所未闻的旋律把我迷住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数学世界之外,还有如此美妙的东西。”
从那以后,他爱上了古典音乐,直至意识到“所有艺术乃至数学都是相通的”。故此,蔡天新也将这段经历视作是大学期间对个人发展影响最大的事情之一,从此,他开启了学理从文、文理兼修的漫漫长路。
拓展阅读
蔡天新:回忆我的大学生涯——老师是关于大学的重要记忆
填志愿,一次既冒险又盲目的“曲线救国”
第一次见到潘承洞先生是1978年秋天山东大学数学系的开学典礼上。厚厚的眼镜(2000多度)、高高的个子(1.84米),是当时44岁的潘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而当时只有15岁的我尚未发育成熟。就在几个月前,潘师因为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由讲师越级晋升为教授。
潘先生正是我报考山东大学的主要原因。我参加高考那年,徐迟发表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此文还被收入到《中学语文》课本。
▲潘承洞
这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是数学家陈景润,同时该文也多处提及另外两位数学家,让他们也出了大名,那便是王元和潘承洞。
原本我就比较喜欢数学,读了这篇报告文学以后,更坚定了把数学作为自己未来专业和人生奋斗目标的信念。可是,陈景润和王元在中科院数学所,那里并不招收本科生,而潘承洞任教的山大每年会在浙江招收二十来名学生。因此,虽然我的总分超出山大录取线不少,我还是打算去山大。
但,那年山大数学系只在浙江招收两个专业,即自动控制和电子计算机,每个专业各招两名学生。因此,我在不识美国数学神童、“控制论之父”维纳是谁的情况下,选择了山东大学的自动控制专业,并被录取。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次既冒险又盲目的“曲线救国”。同时这也说明了,数学和潘先生对我多么有吸引力。
我的勇气也给我带来了不错的运气。山大的自动控制是偏理论的,可以称作控制理论,要学许多基础数学课程。其次,从第二学期开始,在潘师的授意下,全系一年级三个专业(包括自动控制但不包括电子计算机)中挑选出了十七位学习优秀、年龄偏小的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班”。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我选择了比较时髦的计算机专业,那就很难实现跟潘师做数论的梦想了,因为无法入选“小班”。大二暑假来临时,我已基本确定将来跟潘先生做数论,因此潘先生和系里都建议我从自动控制专业转到数学专业,甚至还调整了我的寝室,让我与数学专业的学生同住。
没想到,我换专业的申请被学校教务处拒绝,即便系主任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因此,三四年级我不得不修一些与数论乃至数学都毫不相干的课程,比如最优控制理论、集中参数控制、线性系统理论等,同时也错过了若干数学专业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后者对我能否拓宽数论的研究领域意义重大。
不过,有所失也有所得,大学最后两年,我不仅认识了控制论的命名人维纳和他的理论,同时加深了与同班同学郭雷等的友谊,也做了一回从无线电厂调入山大的彭实戈老师的学生。
1982年7月的一天,我把即将赴中科院系统所深造的郭雷带到潘先生家。至今我都记得师母开门以后,潘先生见到郭雷说的第一句话,“久仰!久仰!”这可是一个大数学家对一个即将离校的本科生说的。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华罗庚
从我决定以数论作为自己专业,到博士毕业前一年,潘先生几乎每年都有大事发生。
1981年,潘先生出版专著《哥德巴赫猜想》(与胞弟潘承彪合著)。
1982年,潘先生与陈景润、王元一起,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83年,他因患直肠癌动了第一次手术。
1984年,潘先生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1986年夏天和冬天先后出任青岛大学校长和山东大学校长(当选院士则是五年以后)。
也正是因此,无论读本科还是做研究生,我都没有机会聆听潘先生的正式授课,他甚至极少有时间来参加讨论班。不过,有一次他来听我们的数学分析课,课后发表讲话,并就课上老师讲的一道例题即兴发挥,推导出了更为深刻漂亮的结果。这一高屋建瓴的思想对我很有启发,在我后来指导自己的研究生时也派上用场。
我在山大念书时,潘先生趁全国数论会议在济南召开之际,邀请华罗庚、柯召等数论大家一同来山大,让全校同学在操场上得见慕名已久的数学传奇人物。那次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华罗庚。陈景润和王元后来还曾来山大出席大师兄于秀源的博士论文答辩会,这些给予全校尤其数学系同学以极大鼓舞。
▲华罗庚
大数学家与学生无拘无束
虽然我把潘氏兄弟的《哥德巴赫猜想》翻得稀烂,却从没有对潘先生取得世界性成就的那几个经典问题做过深入探讨或研究。这是我的两个终生遗憾之一,另一个遗憾是没有和潘先生单独合过影。
众所周知,潘先生在算术级数上的最小素数问题、素数分布的均值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等领域均有开创性的重大贡献。
潘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应该让学生去探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为此,他派大师兄于秀源去剑桥大学,师从大数学家阿兰·贝克研习超越数理论。
而师弟师妹们也各有所长,郑志勇在代数数论领域的工作让他较早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香港求是基金的资助。
张文鹏、翟文广、蔡迎春坚持研究解析数论,分别在L函数均值估计、狄利克雷除数问题、加权筛法的应用等领域有所建树,文鹏并在大西北开垦出一片数论的沃土。
更有远见的是,潘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便意识到数论在密码学理论研究中有用武之地。后来王小云和李大兴开拓出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大兴不幸英年早逝,而小云巾帼不让须眉,破解了包括MD5和SHA-1等数个国际通用的密码,名扬海内外。王小云受聘清华大学杨振宁讲座教授,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陈嘉庚科学奖等奖项。2017年11月,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一类数论函数的均值估计》灵感来自于潘承彪教授来山大讲学时所提的问题,对潘师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但他却亲自推荐给了《科学通报》发表。那是在1984年,此文让我获得了山大首届研究生论文大赛一等奖,也是理科唯一的一等奖。不久,潘师邀请了匈牙利数学家、沃尔夫奖得主爱多士来山大讲学,让我有机会与这位国际数学界的传奇人物关起门来讨论数论问题,他的研究风格和趣味让我一见倾心。
潘先生虽说是大数学家,位居一校之长的要职,却与我们无拘无束,言谈举止时有妙语,多次在中秋和元旦佳节邀我们去他家吃饭。
正是在山大读研期间,我开始并迷恋上了写诗,那自然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没想到潘先生却予以理解、宽容,从未批评过我。甚至在某些场合,还因此在别人面前夸奖我。
1995年春天,潘师来杭州出席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会,住在北山路的华北饭店,我去探望他,并陪他去西湖散步。在白堤上潘师鼓励我说,西湖这么美,在杭州做数学应该是挺享受的。万万没想到的是,仅仅两年以后,潘师便因癌细胞复发去世了,与年长一岁、一年前过世的陈景润一样,享年六十三岁。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