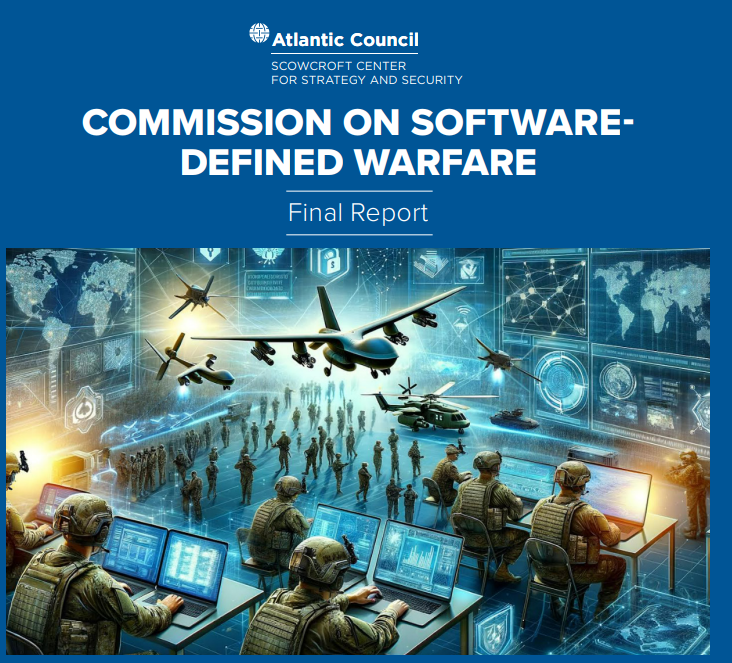全球安全格局的深刻转型为美国带来了冷战以来——或许也是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挑战。地缘环境冲击着美国所谓的全球稳定体系。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多重掣肘——包括经通胀调整后停滞的国防预算、兵员与人才短缺、官僚化的采办流程以及不足的工业产能——严重制约了其快速大规模遏制与应对威胁的能力。
二战期间,美国工业实力与制造能力对盟军胜利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当今美国国防产能已无法满足潜在战时需求。相比之下,其他大国凭借产业政策引导、制造业优势及对软件定义技术(涵盖人工智能、云计算及开发安全运维一体化体系)的战略聚焦,正快速提升国防能力。固守现行国防采办体系——这套无法适应现代技术创新节奏的机制——使美国面临重大风险。这种模式不仅削弱其短期遏制战略对手的能力,更危及在大规模冲突中取胜的潜力。应对这些系统性挑战需要长期持续投入,但当前亟需实施高影响力的近期举措以填补能力缺口、重建优势,这正是本报告提出的"软件定义战争"理念的核心价值。
为何软件定义战争是美军优势的关键?
未来战略优势与冲突威慑的核心要素,在于实现远超对手的跨军种信息共享速度、精度与规模,从而达成指数级提升的决策与机动优势。为此,美国必须将软件能力提升至战略基础地位,与其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相匹配。这不仅意味着部署先进软件系统,更需确保现役软件化平台的及时升级,并实现联合部队异构能力的互联互通,从而以几何级数释放现有军事体系的作战潜能。
软件定义战争
软件定义战争(SDW)为美国国防部提供了一条路径,使其从依赖工业时代实践与遗留软件、以硬件为中心的组织,快速转型为以软件为中心、更能适应数字时代威胁遏制与对抗需求的作战体系。具体而言,在国防部门推行软件定义战争可带来三大战略优势。首先且最为紧迫的是,通过为现役平台(当前军力基础)实施先进软件升级实现效能跃升。这种模式将尖端技术整合至现有平台,既能增强作战人员能力,又可优化成本并延长装备生命周期。其次,软件定义战争对构建未来部队至关重要,后者将依赖自主化、软件驱动且持续迭代更新的能力体系。第三,在全机构推行更高效的软件应用,可显著提升行政与作战流程的时效性与成本效益。
实现这些效益需要开发并运用新型/增强型技术与基础设施、优化流程及人力资本,通过协同效应推动软件解决方案的规模化应用;采用统一标准、开放架构和灵活的数据权管理策略;培养能够更高效获取、整合与运用软件的人才队伍。为成功实施软件定义战争,国防部门必须深化与商业软件产业的合作,特别是在融合现代开发工具与最佳实践的软件研发领域。虽然法律要求国防部门优先采购商业解决方案,但现有体制文化仍倾向于自研而非采购。本报告重点阐述国防部如何更高效利用领先商业软件。需强调的是,这些商业方案必须满足国防系统的严格安全标准,确保作战完整性与抗毁伤能力。
盟友与合作伙伴是美国战略优势的重要来源,在软件定义战争的成功实践中具有关键作用。本报告聚焦于国防部如何优化与加速全域软件采办、整合及应用,同时强化对全球领先的美国商业软件产业的对接。软件定义战争委员会的研究持续强调,国防部需在软件开发、实验验证及集成互操作性最佳实践方面加强与盟友协作。建立协调软件相关活动、整合合作伙伴优势能力的机制,将使美国及其盟友具备应对现有及新兴安全威胁所需的规模效应与互操作性。这种模式对维持战场软件创新的快速迭代同样至关重要——乌克兰战场已印证这一点,而快速创新很可能成为未来冲突的常态特征。
委员会为支持深度研究与论证,访谈了国防部、国防创新生态系统、商业与两用技术行业及美国国会等领域的七十余位关键利益相关方。由此形成推动软件定义战争转型的九项建议如下。
技术
- 构建全域数据中枢并投资人工智能赋能体系
国防部门常务副部长应指示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USec R&E),联合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CDAO)及各军种,加速原始数据的采集、组织、存储与分析,建立标准化接口实现全域数据共享。CDAO需协同USec R&E与各军种首席信息官(CIO),重点投资支撑软件与AI发展的四大支柱——AI就绪数据集、模型与模型卡、DevOps平台及企业级机器学习运维(MLOps)工具——确保最终用户能规模化、透明化、可复现地开发与部署软件及AI系统。
- 确保软件互操作性与集成能力
各军种CIO应强制推行互操作性最佳实践,包括模块化开放系统框架(MOSA,符合《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10 USC 2466a条款)、共享应用程序接口(API)及多供应商环境联合开发参考架构。各军种应设立专职项目执行办公室(PEO),统筹异构能力间的任务集成验证,通过工具整合与仿真推演确保跨任务链技术融合,实现体系化作战(SoS)能力生成。
- 现代化测试评估基础设施
国防部门应授权测试资源管理中心(TRMC)升级仿真环境与数字化测试基础设施,支撑大规模软件与AI赋能平台的快速验证。TRMC需组建联合测试团队,采用DevSecOps流水线的行业最佳实践,重点建立数据反馈闭环机制,通过持续反馈分析实现流程优化、规模扩展与系统性能提升。
流程
- 确立商业软件优先采购原则
推行"商业软件优先"采购策略,要求定制开发需提供充分理由。在需求确认、采办与合同阶段设置早期审查节点,确保充分市场调研与产业对接,并将该原则嵌入国防部政策与培训体系。
- 改革国防部软件需求管理流程
将多数软件需求排除于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JCIDS)流程之外,建立动态精简的需求管理机制以支撑快速迭代式软件开发。组建产业联盟提供商业软件市场情报,每季度与盟友举行技术对话会议,协调共性需求与解决方案。
- 全面解除软件资金限制
国防部主计长应协同各军种财务部门及国会工作人员修订《财务管理条例》(FMR),允许灵活运用研发测试评估(RDT&E)、采购及运维(O&M)等资金支持各类软件活动,从而加速采办流程、提升威胁响应能力并降低风险。在FMR更新前发布临时政策备忘录提供即时指导,同时终止BA-8试点项目。
- 建立关键软件效能指标体系
制定并跟踪所有采办项目的标准化软件指标,通过定期报告机制推动交付速度、互操作性与质量提升。指标体系须涵盖部署频率、平均修复时间、API使用率及用户满意度等维度,将可执行洞见共享至国防部全域以识别瓶颈并优化流程。
人员
- 构建全域软件人才体系
开发覆盖数字与线下学习的模块化分层式软件培训体系,针对不同岗位与任务需求定制课程。深化高校合作并扩展现有国防机构软件培训项目,强化从基础到中阶的软件最佳实践认知及其价值认同,提升软件整合与运用能力。创建软件人才企业交流机制,促进作战人员与产业界协作。
- 全面组建国防部软件专业队伍
招募具备现代开发环境经验的软件工程师(全职/兼职/短期),为软件技术路线、架构设计与商业方案选型提供决策支持。重点部署于首席信息官办公室、项目管理办公室、软件工厂、AI/数据机构及作战司令部等核心岗位。运用特聘专家(HQE)、特聘政府雇员(SGE)等特殊招聘权限及预备役制度吸引保留人才,通过高校合作建立认证人才输送通道,同步修订人事权限与利益冲突规则以吸纳顶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