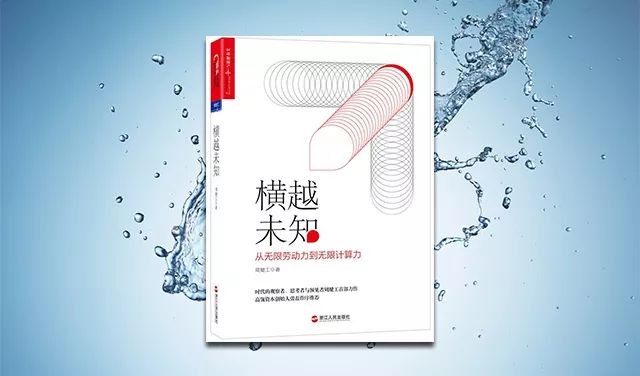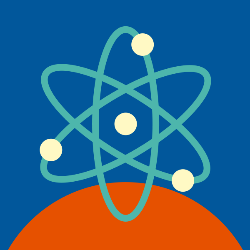科技创新的“月球背面”
关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484篇原创首发文章

对技术的乐观,主导了许多未来学者的态度。最近几年影响力很大的是美国未来学者库兹韦尔(Ray Kurzweil),他断言经济潜在的指数增长力量要远远强于经济周期性衰退。经济衰退(包括萧条)只是暂时地偏离基本曲线。当2045年机器智能超越人类智能时,人类会迎来技术奇点。
在资本市场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一趋势。美国这一轮牛市由科技巨头主导,以苹果公司市值一度突破万亿美元为见顶标志,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的市值,在整个股市中所占的比重增加了。美国公司的利润增加了。与此同时,美国公司在全球上市公司中所占的利润比重也增加了。科技在“吃掉”整个世界。
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中国还是一个穷国的话,今天在互联网的许多领域,至少在应用的层面,中国与美国基本上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可能还有更多领域,譬如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科技,都是如此。而能挤进赛道的国家,也越来越多。通过工业化与技术扩散驱动增长的国家和地区还会包括东南亚、印度等等。贸易和直接投资,是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全球扩散的主要方式。
技术经济学者阿瑟(W.Brian Arthur)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指出: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的确,在技术的驱动下,我们描述经济的表达在不断地演变,如知识经济、新经济、创新经济、数字经济、无形经济。而经济学家对于增长的研究也在跟随着技术与时俱进。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默(Paul Romer),就因为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开拓贡献而受到认可,该理论更加强调创新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首先看经济的层面。移动、云计算、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技术,过去十年改变了整个商业操作系统和经济基础设施,但是经济增长在放缓,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处于“长期停滞”状态。这在经济学家中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一种声音认为,目前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难以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提并论,代表性的声音是美国经济学家戈登(Robert Gordon)的巨著《美国增长的起落》。他认为,从1870年到1970年一百年的历史,也许是经济增长中非常特殊的一段好时光。
为什么我们周围到处都看到“黑科技”,而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中国也是如此。一种解释是,发达国家投资的重心已经转向无形资产,而向有形资产的投资在大幅度下降。下降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边际回报率递减,投资需求大幅度下降。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在发生。
在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如研发、专利、软件、算法、流量、品牌,对于GDP、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目前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应。当然,会有硅谷背景的经济学家站出来说,那是因为经济统计方式落后,没有体现出性价比。譬如,现在一部手机的计算能力,超过了当年阿波罗登月时所使用的大型计算机。又该如何计算免费的搜索、社交、电商、支付服务带来的效率与福利呢?
另外一个原因是科技巨头的垄断性越来越强,妨碍了创新。英国学者哈斯克尔和韦斯特雷克(Jonathan Haskel, Stian Westlake)新近的畅销书《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并非这些公司不创新,而是因为技术的外溢效应,在巨头与新生创新公司之间是不对称的并且有利于前者,这样导致整个社会的创新速度放缓。
其次在社会层面。技术带来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增长必然带来贫富差距的扩大,更高的效率也会带来更为悬殊的差距。科技带来了效率的极大提升,我们可以看到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加大,而前者比后者更甚。这种差距的扩大,一方面是新技术创造的新就业对于原有就业岗位的冲击,另外一方面是现有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兴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会更加有利于少数成功者,以及少数极其成功的公司。
如果从全球总人口数来看,工业化与技术在中国的迅速渗透,取得了巨大减贫成果。但是,如果深入到一个个国家的内部,主要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常年停滞甚至下降。在向新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种现象是否会在中国出现,很值得关注。
最后是在政治层面。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失落、内部贫富分化、身份政治盛行,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政治行动。而中国和美国中产之间的竞争,已经在科技领域展开。互联网和算法彻底改变了媒体与传播,在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中助长了民粹化的倾向,并且已经在选举和投票中产生了两极化的结果。

毫无疑问,技术始终带来新的机会。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13亿人口没有用上电,这显然不是技术的原因。也许技术的扩散和分享,比产生新的技术更加重要。新兴的技术,可能在落后的地区得到更快的应用,例如移动支付在非洲一些国家普及的速度更快。那些贫困地区有可能通过风力/光伏加上储能的分散式电网,解决用电问题。也许各种日益智能化的技术,仍然处于向整个经济渗透的早期,并且刚刚开始向其他行业转移,令我们去期待一场整个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历史告诉我们,让经济增长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唯一原因,就是工业革命,而目前日益占据主流的经济学家也相信,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但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机会和利益,却往往成为人类冲突的根源。政治家往往很难为长期的趋势做出决策。互联网让技术的传播与分享更加便捷,让开放协同的创新更加有效率,但全人类依然生活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中,国家利益阻止了全球采取集体的行动。在国家的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以及更加多元化的团体,都在网络世界中形成与裂变,政治家与政治体制在秩序与自由、效率与公平,做出动态的平衡与取舍的难度也增加了。
(本文作者系著名媒体人,曾任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和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CEO,先从事投资与创作。著有《横越未知》等著作)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 图片 | 视觉中国 」
秦朔朋友圈微信公众号:qspyq2015
商务合作:biz@chinamoments.org
投稿、内容合作、招聘简历:friends@chinamoment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