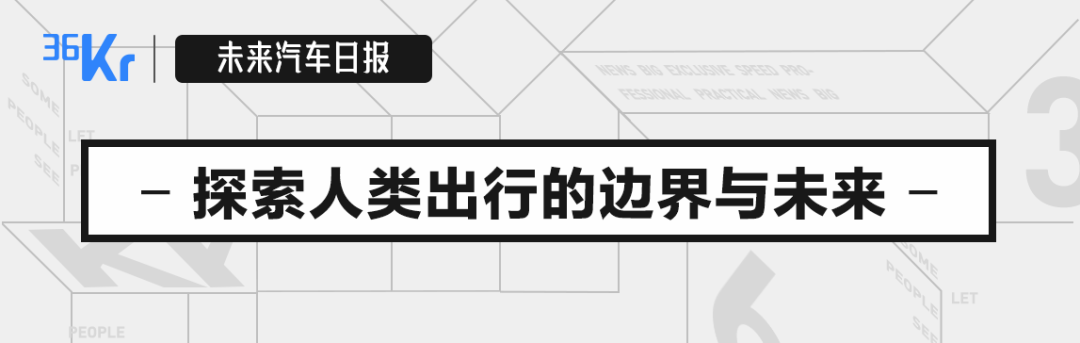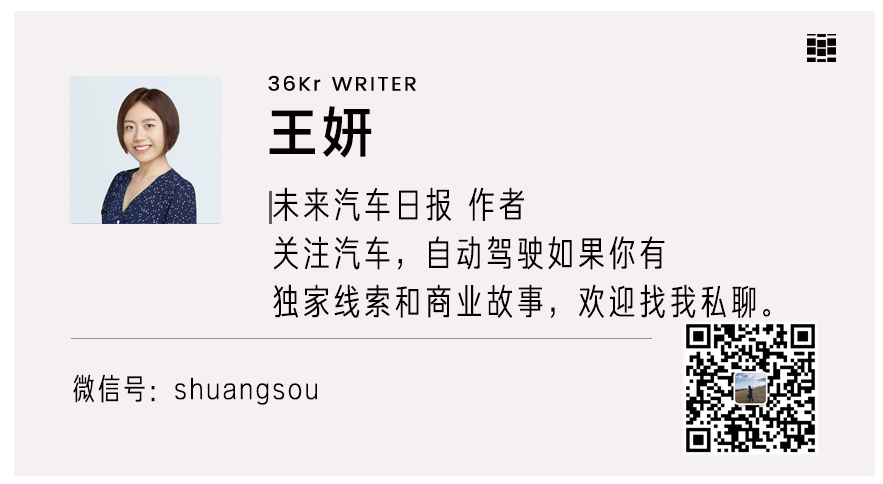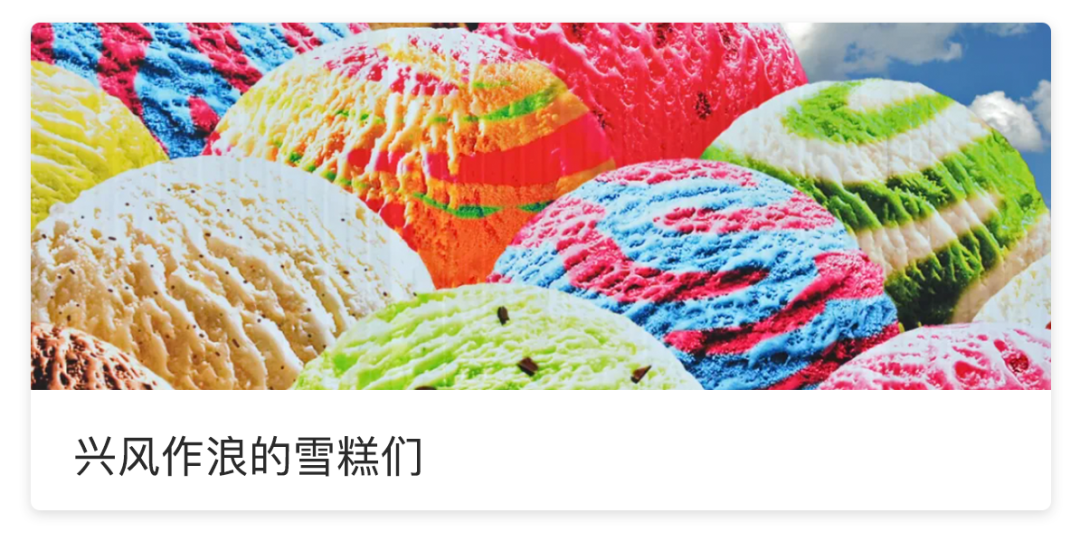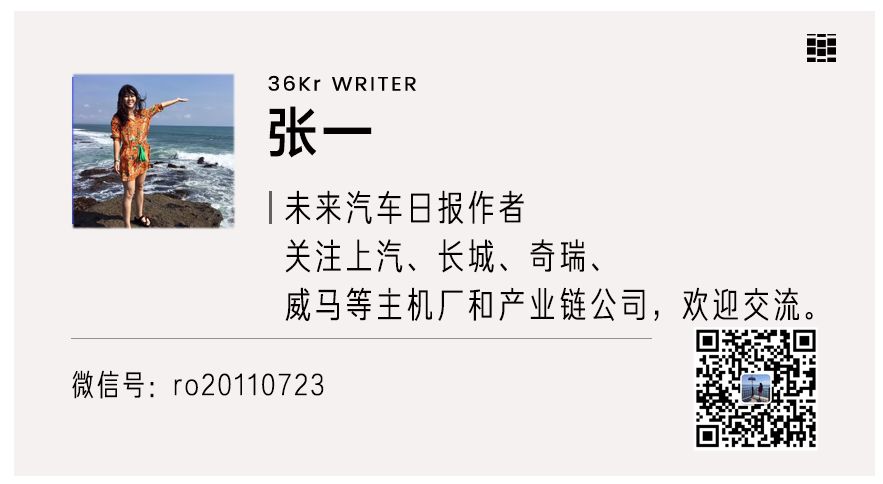![]()
来源 | 未来汽车Daily(ID:auto-time)
![]()
“我只想报复性攒钱”
37岁生日那天,程涛对着蜡烛许了两个愿:要回被拖欠的工资,重新找到工作。
这是难得轻松的一天,老家的父母一大早打来电话,妻子从早忙到晚准备了一大桌家乡菜,乖巧可爱的女儿陪在身边。他极力避免回想过去一年的糟心经历,但还是很难维持片刻的好心情。
中年人的肩膀上压着太多责任,一家老小都指望着他养活,但程涛几乎每一天都在为钱发愁。在这位被欠薪裁员半年多的造车新势力前员工的心里,就算把失败、艰难等描述现实的负面词语全部加在一起,都不足以形容自己对36岁这一年的感受。
女儿出生时,程涛和妻子咬牙买了一套每平方米5万元的小两居学区房,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每个月还背着1万多元的银行贷款和朋友借款。他从农村一路摸爬滚打到大城市,没有亲人帮衬,立足扎根的一切都要靠自己挣得。收入来源中断后,这笔数目不小的钱成了最大的问题。
![]() 程涛从家乡返城的沿途 来源:受访者供图
程涛从家乡返城的沿途 来源:受访者供图
“最近经常看到人们说报复性消费,但我只想报复性赚钱攒钱。”作为家庭经济支柱,长达半年多没有收入让程涛的生活彻底被打乱了。
为了开源节流,程涛和妻子已经很少外出吃饭。去年底的结婚纪念日,夫妻俩的庆祝方式是带着女儿看了一场动画电影。过年回家的交通工具从高铁变成了普通火车,女儿时常问起的迪士尼出游计划,已被无限期搁置。
![]() 程涛结婚纪念日带孩子看电影 来源:受访者供图
程涛结婚纪念日带孩子看电影 来源:受访者供图
压力太大,过去一觉睡到天亮、连女儿哭声都听不见的程涛,开始被失眠纠缠。日渐增多的教育和生活开销压得他喘不过气,两鬓的头发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灰白色。
在造车新势力工作不到一年的李佳一度不敢接父亲的电话,怕家人察觉到自己被裁员。他来北京那一年,55岁的父亲仍在继续外出打工,想为儿子的成家立业再出一份力。
孙浩向交往不久的女朋友暂时隐瞒了失业的消息。母亲从老家来看他,他不得不假装每天早起出门上班,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找个咖啡馆待一天,挨到晚上下班时间再回家。“以前看电视剧里演,有的人下班即使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一会儿,我发现现实里真的会这样。你不能把这种压力带回家里,但你也不知道怎么排解。”
所有的耐心、自信和自我保护能力,都在跟老板和HR的周旋中逐渐消耗殆尽。
程涛听说有人在领导办公室“撒泼打滚”要到了一部分工资,他自己豁不出去,就在下班时间买了水果去领导家里拜访。他当时对双方坐下来和气说话的氛围很满意,回到家告诉妻子讨薪有望。但现实是,谈好补发的工资并没有兑现。他在彻底失望后决定选择劳动仲裁,但公司不同意调解,“你只能上诉,要拖很久,要想清楚”。
走到最后,程涛发现即使自己是有理的一方,“员工的胳膊也拧不过公司的大腿”。
不少被裁员工一开始不服气,准备跟公司叫板,但很少有人能真正撑到“来真的”那一天。走法律程序或劳动仲裁意味着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孙浩甚至开始羡慕被大公司裁员的难兄难弟,“至少他们还能正常拿到工资和赔偿”。
运气好的人去年提前离职,无论满意与否总算能找到下家。到2020年,受疫情和汽车行业不景气的双重影响,找工作难上加难。
孙浩每天都宅在家里刷招聘网站,简历投递的方向也不限于本专业,他渴望得到更多的面试机会。少出门既是为了尽量避免新的开支,也因为昂贵的房租,“多待在家里能让自己心里觉得值回房租”。
![]()
被生活“开了个大玩笑”
卫生纸少了,洗手液稀了,食堂的菜色每况愈下,连原本人手一个的垃圾桶数量都在缩水。当初奔着高薪和前途来到造车新势力的传统汽车人,就像被生活“开了个大玩笑”。
2018年初,最早推出“准量产版车型”的5家新造车公司之一奇点汽车,在北京丽都酒店举办年会。十几名总监级管理层每人自掏腰包2000元,给员工购买耳机、按摩椅、加湿器等礼物,六七百人参与抽奖,士气高昂。
![]() 奇点汽车年会现场 来源:沈海寅微博
奇点汽车年会现场 来源:沈海寅微博
一家六七百人规模的知名新造车公司的年会也同样声势浩大。一位曾参与当年年会的员工告诉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中奖率能达到约80%,奖品有苹果系列产品,最小的是666元红包,最大的是5万元现金,“真的有点颠覆了我对年会抽奖的认知”。2019年,这家公司的团队规模达到了2000多人,在成都、上海、温州三地分开举办年会,隆重程度跟2018年不相上下,“奖品中增加了一年和二年的新车使用权”。
但到了2020年,这家知名新造车公司的年会失去了上一年的“热闹和气派”,只是在上海简单办了场运动会,“吃的是盒饭,人均40元左右”。同一年,深陷欠薪泥淖的奇点汽车也没再举办年会,只有零星的部门小范围聚餐,员工人数也缩水大半。
无数个缺钱的细节,拼凑出造车新势力捉襟见肘的尴尬现状。
未来汽车日报去年12月参加天际汽车ME7下线活动时,天际汽车食堂提供至少四菜一汤,荤素搭配,另有水果可选。当时公司内部人士介绍称,天际汽车引入了两家食堂供应商,以保证员工饭菜质量。到今年4月,被欠款数月的食堂老板撂了挑子,饭菜质量一落千丈。
另一位造车新势力员工称,该公司出差预算从去年开始明显卡得严格了。“限制要求多了,出差周期延长了,比如要求员工半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返回。”
因为没钱,造车新势力产业链上游的供应商往往规模小、资金池小、回款周期短(传统车企回款周期通常半年左右,新造车可能压缩到1个月以内)。
一位造车新势力供应商向未来汽车日报透露,有的供应商在签合同时按照大采购量大幅让价,但生产线铺开后发现,厂家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达到原定的采购量。新造车内部人士称,“乐视汽车出事之后,供应商对造车新势力心理上就有提防了。”
一位负责采购的造车新势力员工告诉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有的供应商建在农村,公司都没有牌子,看门的是位老大爷,“看起来就像是个农家乐”。另一位主机厂资深从业者则表示,对于造车新势力而言,想找齐整车生产所需的零部件供应商,并让他们愿意供应、准时供应,不是容易的事。
奇点汽车整车项目曾因欠供应商账款,导致一批定制生产的加工件出现断供。拜腾汽车也因融资和供应链问题造车“搁浅”。
一位曾两度参观拜腾汽车的人士表示,到去年年底,拜腾只对外开放了展厅和研发大楼,工厂大部分还是空着的,“还是只有一台样车”。
![]() 2019年年末,拜腾汽车南京办公楼一楼展厅 来源:受访者供图
2019年年末,拜腾汽车南京办公楼一楼展厅 来源:受访者供图
缺钱也波及产业链下游的整车销售。新造车品牌因为车卖得少,跟预期差别很大,合作的经销商配合度也低。如果出现客户投诉的情况,新造车公司厂家的人要亲自去服务客户,处理客户投诉问题。
寒冬持续蔓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不只是造车新势力。
过去出差选八九折机票的丰田(中国)也收紧了预算,出差前三四个小时内有更低折扣的,就要选更便宜的航班。特斯拉也一度向出差预算下手节流,“住宿酒店降到400元左右的快捷酒店,时常全球参加比赛、提供技术支持的技师也不怎么出差了”。
某合资车企去年一个工位一个垃圾桶,现在四个工位共用一个垃圾桶,就连洗手液也变稀了。
一位主机厂员工告诉未来汽车日报,部分车企生产线工人兼职送起了外卖。
![]()
从高峰滑下,然后突然卡壳
从某合资品牌跟随前领导一起加入造车新势力的孟桐至今记得,几位同事一起离职的部门散伙饭上,大家都喝多了。
虽然抱着各自不同的人生追求,但至少在当时,离开的人看起来前途无量。有的升职做管理层,有的拿到了相当可观的薪水,“大家都对未来充满了干劲”。最后举杯时,留在传统车企的同事开玩笑,“苟富贵毋相忘,以后去抱你们的大腿”。
有人打工遇到了天花板,需要新的创业体验,也有人受够了传统企业的论资排辈。薪资水平、响应速度和晋升空间向互联网公司看齐的造车新势力,展现出了风口上的力量。
2015年,向电气化发起号角的传统车企和起初顺风顺水的造车新势力互相挖人,在传统车企工作多年的程涛曾经是这场人才战中的受益者。
当时,大多数新造车企业还处于组织成长、人员招聘的阶段,总人数在200-300人,有些甚至不足100人,真正意义上的研发团队尚未组建起来,正是高薪招揽人才的关键时期。蔚来财报显示,2016年全年,蔚来汽车员工薪酬成本是9亿多元,到2018年已增至41亿元以上。
风头正劲时,有的新造车企业甚至开出比传统车企高出3-4倍的工资找猎头挖人,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职级和待遇水涨船高。以至于程涛在得知同行跳槽的待遇后,后悔自己当时答应得太快,没有在伸出橄榄枝的诸多公司里多加比较。
那是汽车业黄金时代的尾声,终端销量屡创新高,补贴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初露峥嵘。人们坚信,这将是一片能复制互联网行业奇迹的沃土。
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细节,包括蔚来汽车花费数千万元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举办的首场NIO DAY,以及斥巨额租金开设的北京王府井NIO House。蔚来汽车员工在国内一线城市的差旅酒店标准为900元,向世界500强看齐,出差上海可以直接住希尔顿;每天300元的出差补助如果花不完,可以转成津贴直接打进员工账户。
![]() 蔚来汽车NIO DAY 2018 来源:蔚来汽车
蔚来汽车NIO DAY 2018 来源:蔚来汽车
传统车企员工李超承认,这些看起来酷炫时尚、拥有无限想象力和发展空间的新机会,对于在职场摸爬滚打5年的热血青年来说,“无论哪一样都很有吸引力”。
他之所以没去抓住这个机会,是因为新造车“过热了,感觉不太靠谱”。
新造车这个堪称“钞票粉碎机”的游戏注定依赖资本输血,随着资本的热情逐渐冷却,滑过创业浪潮的最高点,风头一时无两的新造车运动就像坐上了过山车,一路滑向难以预测的方向和终点。
2018年上半年,到了概念车推出2-3年后交作业的时间,“很多人交不上来作业”,一位2016年跳槽去新造车公司的汽车人称。
在孟桐看来,当热闹非凡的融资环境不再,缺钱的新造车就像是突然被卡壳,“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实现,也不给机会继续去做了”。
从2018年开始,造车新势力在项目开支上明显收紧了口子。
一位造车新势力员工透露,部门培训项目预算申请时,审核经理挨个给几家备选公司打电话进一步压价,缺钱严重的企业项目进展停滞,“供应商都选好了,但是没有下文了”。还有的车企把以前分给第三方咨询公司做的工作接管过来,亲自操刀。
蔚来主管质量、采购、制造的执行副总裁沈峰对36氪表示,他出去开会都会关掉办公室的灯。2019年下半年起,蔚来安亭总部办公楼内竖起了节约用电的提示牌,每天午休时间熄灯1小时。
从去年8月开始,程涛注意到工资发放开始变难,公司给出的说法是融资没能进来。身边的同事走了一茬又一茬,每个月都有同事离开,三个人的岗位变成两个人,最后变成一个人。程涛也想过撂挑子,但又抱着公司或许能断臂求生的侥幸心理留了下来。
有人及时止损,他说服自己要有始有终。但直到大年三十儿,捧着手机等了一天的程涛也没等到原本说好要补发的工资。
![]()
在99%的质疑中活下来?
2014年左右,曾在一家日系车企工作三年的张鹏从传统主机厂出走,跳槽到一切从零开始的造车新势力。
入职第一天,他就从办公桌的陈设上感受到了明显的落差。在传统车企工作时,桌上井井有条地摆放着订书机、文件夹、计算器、笔记本、签字笔和一包纸巾。但在新造车企业,“办公桌上只有笔记本和一台电脑”。
辗转于几家造车新势力的这几年,张鹏经常熬夜加班整理材料,而在传统车企,“这些材料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简单修改”。
另一位接近新造车的人士也对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表示,很多在传统主机厂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新造车公司都不具备,需要员工自己想办法解决。比如试制车下线测试需要有道路测试场,传统车企都有专门的场地,但是新造车公司需要员工自己协调,跟合作伙伴借用场地。
进入2020年,融资窗口关闭、亏损持续和疫情黑天鹅的打击,让雪上加霜、四面楚歌的新造车势力,已很难留住昔日重金招揽的人才。
蔚来汽车前用户发展副总裁朱江,将于6月1日正式加盟福特中国担任MACH-E纯电项目负责人,回到久违的传统主机厂怀抱。今年3月,蔚来汽车前用户中心副总裁赵昱辉入职长城汽车,担任长城销售公司用户中心总经理。2月底离职的原天际汽车董事、首席营销官向东平,也已出任北京现代副总经理、销售本部长。
一位在造车新势力工作多年的汽车人告诉未来汽车日报,身边有人脉的基本都回到传统主机厂了。“造车新势力就像一艘在大海上航行的船,随时可能被打翻,传统车企更像是航母,更稳。”
享受了新造车巅峰时刻的激情,踊跃进场的汽车人正在承受当下潮水褪去的痛。
因为“不习惯”,孟桐在新造车公司只待了两个月就回到了老东家。“抛开薪水不说,业务上的预算差距非常大,工作的流程化和分工也不够清晰。另一方面,因为体量小,对接一些零部件厂商也没有议价权,没有人信任你,这个落差非常大。”
张鹏则有些后悔。如果当初没离开日系车企去“趟新造车的浑水”,他现在“起码是课长级别,还能冲一冲六七十万的年薪”。
他现在全职在家带了大半年孩子。受疫情黑天鹅突袭,传统车企的招聘通道春节后骤然关闭,他四处寻找门路试图跳回传统车企,硬着头皮和刚毕业不久的职场新人竞争为数不多的几个岗位,预期只能拿2万元左右的月薪。
当初为之投入的梦想和抱负早已消耗殆尽,只剩现实的一地鸡毛。张鹏觉得,“现在应该不会再有人去造车新势力趟这趟浑水了,除非实在找不到工作”。
程涛原本以为凭他的资历找一份工作问题不大,但因为和前东家的拉锯战,失业时间不断拉长。他甚至第一次萌发了离开汽车业的想法。“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公司里的螺丝钉,这个公司或者行业不景气的时候,不管你能力行不行,都有可能像大浪淘沙一样,一个浪过来就把你带走了。”
他到这时才意识到,美剧《权利的游戏》中那句意味深长的台词“Winter is coming”,成了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接到最新一次面试机会后,他告诉自己另一句话:“你会失败的,而且不止一次,你要有耐心。”
这是几乎所有新造车人的困境和机会。李斌和李想仍在为造车倾注心血,何小鹏觉得,新造车创业的乐趣就是在99%的质疑中最后活下来并长大。1月19日,威马汽车创始人沈晖在50岁生日这天写道:这一年白头发又长了不少,艰难的时刻也都咬牙坚持过来了。
生活的鞭子或许还会抽得更狠一些,但他们总得继续向前。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程涛、李佳、孙浩、孟桐、张鹏、李超均为化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