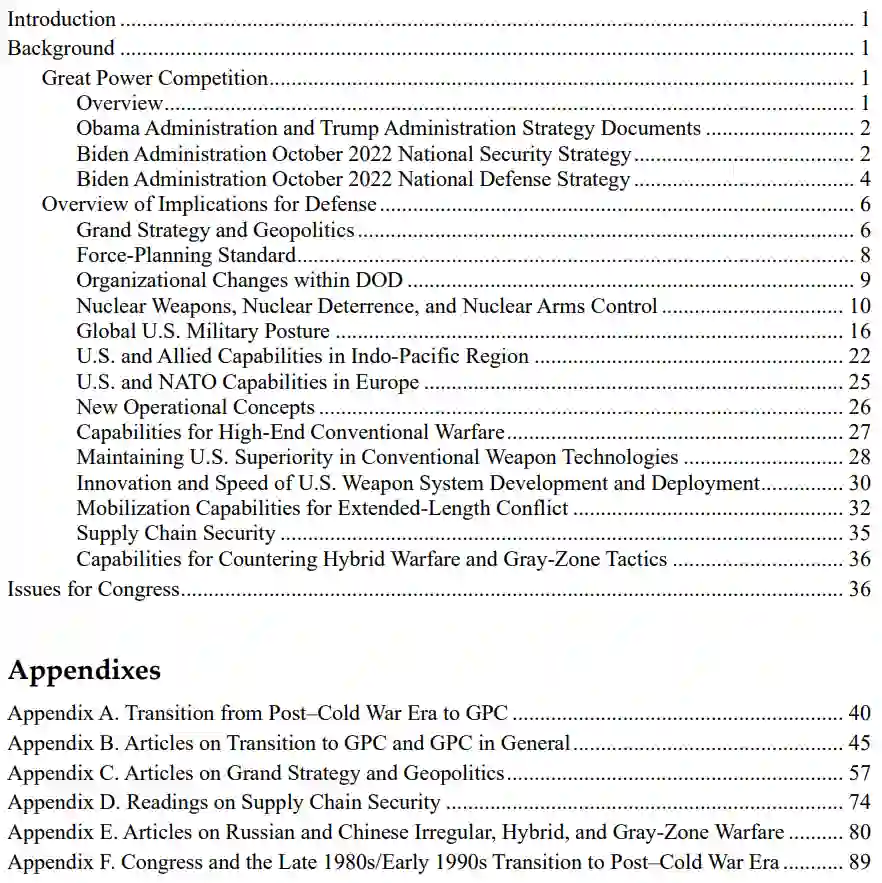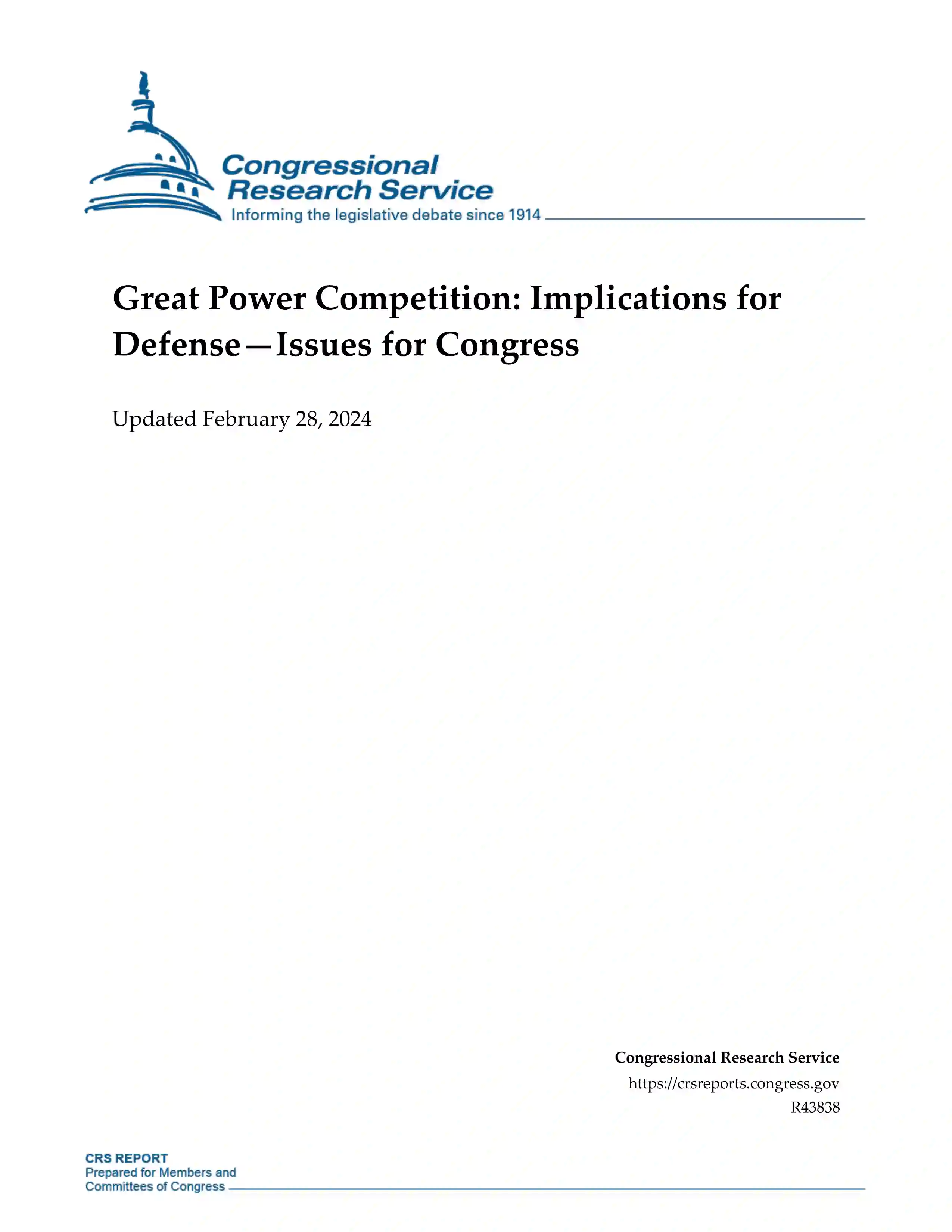在过去十年中,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的竞争加剧--通常被称为大国竞争(GPC)或战略竞争--深刻地改变了后冷战时代有关美国国防问题的讨论:反恐行动和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袭击事件后一直是美国国防问题讨论的中心,现在已不再是讨论的重点(但仍然存在),讨论现在更多地集中在以下因素上,所有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中国和/或俄罗斯有关:
- 将大战略和地缘政治作为讨论美国国防问题的出发点;
- 兵力规划标准,即美军规模应能应对的同时或重叠冲突或其他突发事件的数量和类型--这一规划因素会对美国国防预算的规模产生重大影响;
- 美国防部内部的组织变革;
- 核武器、核威慑和核军备控制;
- 美国的全球军事态势;
- 美国和盟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能力;
- 美国和北约在欧洲的军事能力;
- 新的美军作战概念;
- 进行所谓高端常规战争的能力;
- 保持美国在常规武器技术方面的优势;
- 美国武器系统开发和部署的创新和速度;
- 长时间大规模冲突的动员能力;
- 供应链安全,即美国军事系统对来自非盟国,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的部件、子部件、材料和软件的依赖性的认识和最小化;以及
- 打击所谓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战术的能力。
美国国会面临的问题是美国国防规划和预算编制应如何应对全球战略优先权,以及是否批准、否决或修改拜登政府的国防战略和为应对全球战略优先权而提出的资金水平、计划和项目。国会对这些问题的决定可能会对美国国防能力和资金需求以及美国国防工业基础产生重大影响。
成为VIP会员查看完整内容
相关内容
Arxiv
224+阅读 · 2023年4月7日
Arxiv
23+阅读 · 2020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