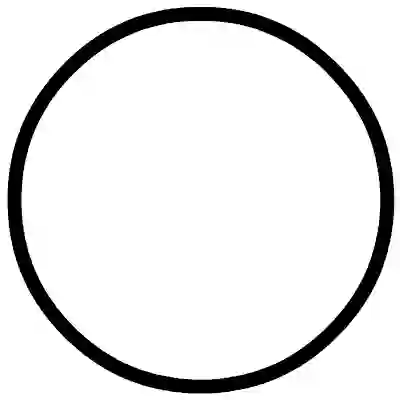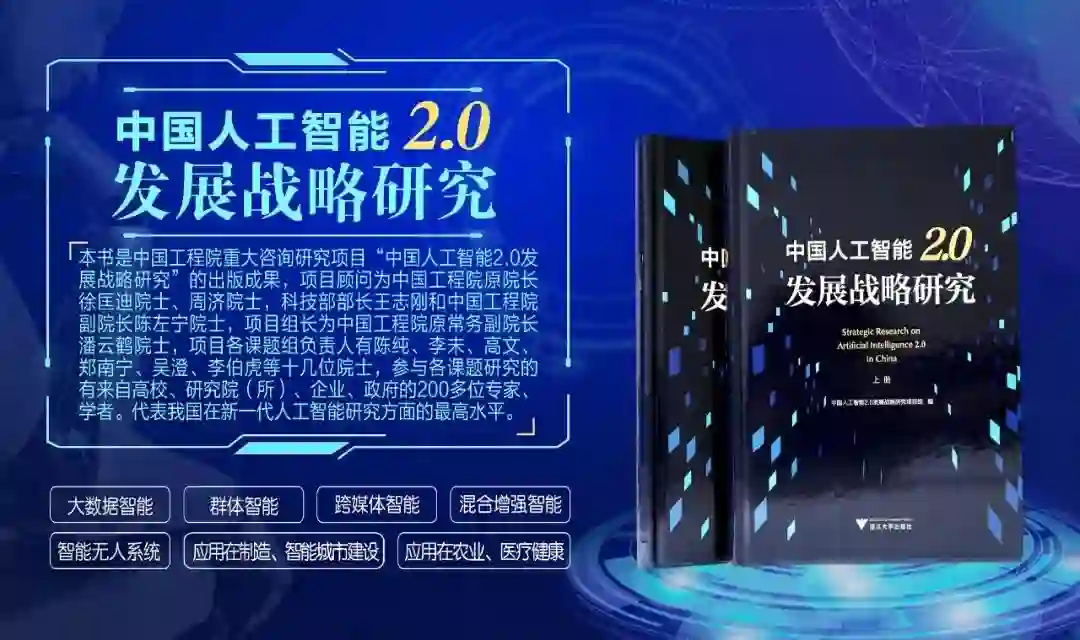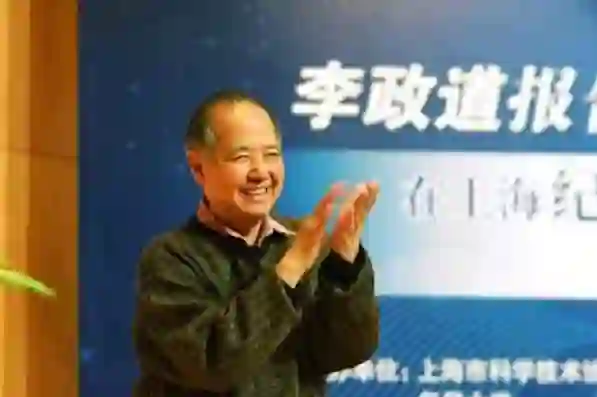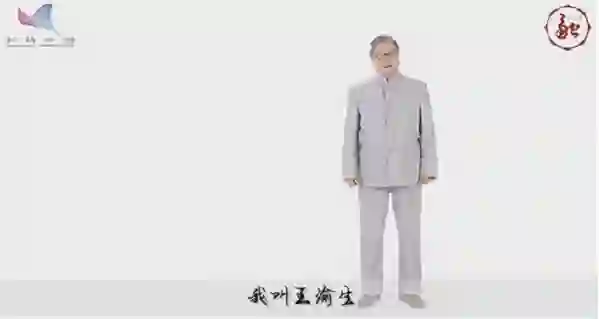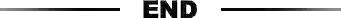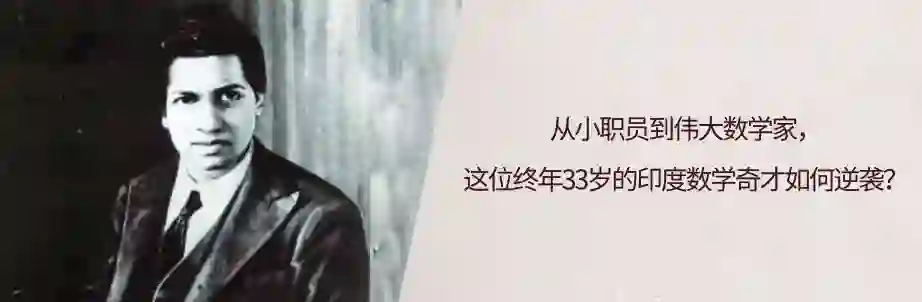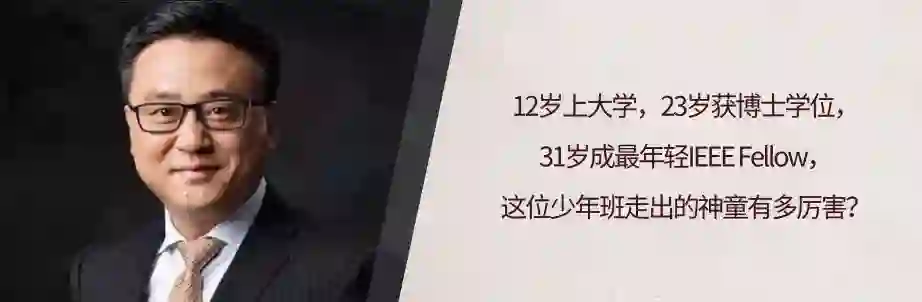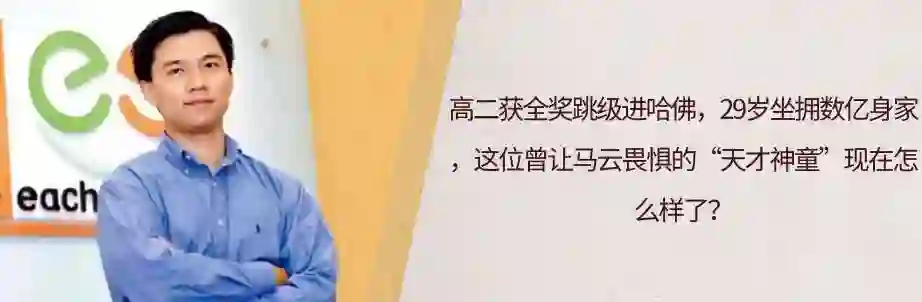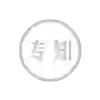李政道为什么说科学研究是条鱼?
人工智能进入2.0时代,你还在原地等待?
点击图片立即上车!
黄旭华,男,汉族,1924年2月出生,广东汕尾人。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名誉所长。1958年起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总设计师突出贡献奖,被评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十大海洋人物”、“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
要想不再受欺负,中国得强起来
问:您曾说:“我的人生,就是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里决定的。”可否分享一下您弃医从研、科学报国的经历?
黄旭华:我本是想学医的,因为父母都是医生,后来事情逐步发生了改变。我小学毕业时抗战爆发,学校基本都停办了。当地的爱国青年组织了一个抗日救国宣传队,我们就跟着一起搞宣传,演了一部话剧《不堪回首望平津》。当时来的人很多,密密麻麻,广场上都挤满了。我们在台上演抓汉奸,底下喊“杀”“杀”,那时我就想大家对日本人恨死了,长大了一定要为国家尽点力。后来我到桂林念书,日本人炸桂林,那是满城狼藉、一片废墟。每次警报一响,就得出城躲进防空洞。如果早上发警报,晚上还没解除,就得在山沟里挨一天饿。每次我跟着大家从城里往外跑就一腔怒火,有三个问题始终在心里浮现:为什么日本人这么疯狂,想登陆就登陆,想屠杀就屠杀?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安居,一定要到处逃亡?国土那么大,我们跑来跑去,连一个安安静静读书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什么道理?我请教我的老师柳无垢,她给我的答复很简单,就是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人家宰割。于是我将原名“绍强”留给二哥使用,给自己起名“旭华”,意思是中华民族必定如旭日东升一般崛起,我要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做贡献。后来我到重庆考大学,和国民党空军航校的一位朋友交流了很多,这个时候我就彻底改变了。我认识到,要想不再受欺负,中国得强起来。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将来制造飞机保卫我们的蓝天,制造军舰抵御外国侵略。后来我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
别人问我对共产党是怎么看的?
我说就是“山那边哟好地方”“没人给你当牛羊”
问:解放前夕,还在交大求学的您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中共地下党。可否讲讲您的入党经历,特别是您对党的认识过程?
黄旭华:我在交大读书期间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山茶社”,通过这个组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又组织了一个文艺社团“大家唱”,每周教大家唱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首歌对我影响很大,叫《山那边哟好地方》,歌词叫“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给你当牛羊”。这首歌让我感到,山那边是个好地方,这里的人过得非常愉快,安心搞生产,没有剥削,一片安宁繁荣。你问我对党对共产主义最初的认识,就是“山那边哟好地方”,“没人给你当牛羊”。
后来有一次,我们社里一位姓陈的同志跟我聊天谈了好多,说你对共产党是怎么看的。我说就是“山那边哟好地方”,“没人给你当牛羊”。他说你要加入共产党吗?我大吃一惊:“加入共产党?党在什么地方,我都不晓得!”他说:“你好好考虑,如果你想加入共产党,你写一个报告给我,我帮你递上去。”我问道:“你是党员吗?”他说:“我是地下党。”1948年冬天,我写了一个报告。直到1949年春节,“山茶社”一位叫魏瑚的同志,他说党批准你加入党。我入党是这样过来的。我对党的确也还没有更多概念,很迫切地想要增加党的知识。后来组织上派我去党校学习。我读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等。我开始下定决心,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共产主义的理想需要我们一生去努力!
核潜艇研制过程充满挫折,
项目上马下马,我没有动摇过
问:您又是怎样与核潜艇研制事业结缘的?
答:大学毕业后,我党政工团都走了一遍,最后还是要求回归科研,于是到了刚刚成立的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后来当上了设计二处潜艇科科长。1958年,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报告,建议研制导弹核潜艇。海军跟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联系,把我调过去。当时只告诉我到北京出差,有些事需要帮忙,一到北京就把我留住了。我当时非常兴奋,因为对常规动力潜艇我就感觉一切都是新的,核动力潜艇那更是世界上尖端的尖端。能够从事这份事业,为国家服务,我非常激动。我一进去就下定决心坚持干下去。当时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并不具备研制核潜艇的条件。毛主席高瞻远瞩,说了一句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大大坚定了我的决心。在核潜艇研制过程中那么多挫折,项目上马下马,我都没有动摇过。
要反对原子弹,自己就应该先拥有原子弹;自己有了原子弹,必须要有执行第二次核打击的手段,这就是核潜艇。
问:中国为什么必须要有自己的核潜艇?
黄旭华:居里有一句话:“要反对原子弹,自己就应该先拥有原子弹。”我加了一句:“自己有了原子弹,你必须要有执行第二次核打击的手段,这就是核潜艇。”为什么?有了原子弹,你声明不首先使用原子弹,那你把原子弹摆在地上让人家打也不行。必须拥有核潜艇,把原子弹埋在水底下。
讲到潜艇,两次世界大战,潜艇的威力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它潜入水底,隐蔽性强,给敌人的军舰和海上运输造成很大的威胁。据统计,一战中被潜艇击沉的海上运输船队占总损失的87%。一战结束后,大家对潜艇重视了,防潜的技术开始出现,潜艇在水下的隐蔽性大打折扣。就算这样,二战中被潜艇击沉的海上运输船队仍占总数的67%,交战双方被潜艇击沉的航空母舰达17艘。那个时候潜艇在水下靠蓄电池航行,而蓄电池能量有限,功率也不大,在水下速度很慢,全功率航行大概只能维持一小时,慢慢走可以维持一到两天,一到晚上它要浮起来,有一个通气管,启动柴油机,一边低速航行,一边给蓄电池充电。
二战结束后,大家逐步研究,终于找到了一个不需要空气的动力能源,这就是核动力。有了核动力,潜艇就有了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它不需要空气,能长时间埋伏在水下;第二,反应堆功率大,航速大大提高;第三,反应堆一次装载核燃料,全功率燃烧的周期是一周年,现在已经发展到跟潜艇的寿命同周期,也就是说装一次燃料就再也不用装了,这也就大大提高了潜艇的续航里程。美国1954年把反应堆用到潜艇,成功建了第一条核动力潜艇,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这个核动力潜艇,是海军作战的杀手锏。如果装上了巡航导弹,它就是航空母舰和大型军舰的克星。如果装上了洲际导弹,那它的打击面可以覆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敌人首先对我进行核攻击的情况下,我可以保存自己,给他致命的核反击,叫做第二次核打击。和平时期有了它,就可以遏制敌人的核讹诈,保卫国家,维护世界和平。所以毛主席讲“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第一,我们中国需要核潜艇;第二,核潜艇技术困难,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出来;第三,表示我们的决心,非搞出来不可。
任何复杂的尖端技术都是在常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是常规的综合和提高
问:美国发展核潜艇是“三步走”,我们采用水滴线型,将“三步”并作“一步”,并突破了核潜艇最为关键的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等7项技术,被誉为“七朵金花”,可否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黄旭华: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常规动力潜艇经常浮到水面,艇的形状只要适合水面航行就行,核潜艇长期潜在水底,必须找一个适合在水下高速航行的技术。美国为此分三步走:第一步,艇体保持不变,集中全力搞核动力;第二步,造了一个常规动力潜艇,采取水滴线形,探索水滴线形在水下航行的性能;第三步,把核潜艇搞成水滴线型。
美国分三步,我们分几步?好多专家提出,美国比我们强得多,它分三步走,我们至少分五步、六步。但回头想想,人家已经走成功了,你不用再去探讨这条路是不是可行。从理论上分析,水滴线型的截面都是圆的,圆的周边最短,跟水接触的面积最小,产生的摩擦阻力也最小。但它的操纵性能如何,我们心中无底。我们造了一条25米长的仅容一人的小潜艇,没有任何记录仪表,看看在水底下怎么样。有一个常规潜艇艇长,他自告奋勇下去操作,在底下跑了好多圈,然后上来了:“好操作!”这时我们才彻底放心。
核潜艇长时间埋伏在水底,我们自然就想到要解决人的生活条件保障问题。第一个就是空气保障,所以我们“七朵金花”有一朵金花叫做人工大气环境。水面上它有导航设备,通过无线电、卫星等导航。在水底下,你不可能说我浮上来导航,那不行。怎么办?你首先要能发现敌人,知道它的位置,然后你的鱼雷才能发射。其中包括一个被动的一个主动的。被动的就是敌人老远有点声音我就发觉到声音,但是光发觉声音不行,还得知晓它的距离和方向。通过主动发出一个声波,用声波回来这个时间就能计算距离和方向。这个要求很高,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七朵金花”就是这样一朵一朵解决的,不是无中生有。所以尖端并不神秘。综合就是创造,综合能出尖端。任何复杂的尖端技术都是在常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常规的综合和提高。技术不发达的国家,可以由常规的基础上发展尖端。
我是总设计师,我不仅仅要为核潜艇的安全负责,更要为艇上170多个参试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到底
问:核潜艇是否具有战斗力,极限深潜试验是关键。1988年,64岁的您亲自登艇参与深潜试验,您为何要以身试险?
黄旭华:所有的潜艇研制完成后,都有一道严峻考验,这就是进行极限深潜试验。1963年,美国某王牌核潜艇深潜试验还未到200米就沉入海底,艇上100多人无人生还。这艘由里到外全由中国人白手起家研制的核潜艇,能否顺利闯过中国核潜艇研制史上第一次深潜试验大关,参试人员心中无底。个别人给家里写信,说万一回不来,有这样那样未了的事,请家里代为料理,其实就是遗书,宿舍里有人在唱《血染的风采》。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去执行深潜试验,那是非常危险的。
我决定同他们对话。我说,随时随地准备为国家的尊严和安全献身,这是战士的崇高品质。但这次深潜试验绝不是要我们去光荣,而是把试验数据一个不漏拿回来。我们在设计上留有足够的安全余量,试验程序是由浅到深逐步进行,下潜绝不蛮干。在万无一失情况下,也可能存在意外危险,比如我们工作中有一丝疏忽,或者存在超出个人知识范围之外的潜在危险。说句实话,我既有充分的信心,又十分地担心。怎么办?我决定跟你们一道下去,共同完成深潜试验。好心人劝我,说艇上不需要你亲自操作,你的岗位是坐镇水面,何必冒险下去?我说我下去不仅可以稳定人心,更重要的是在深潜过程中万一出现不正常的情况,可以协助艇上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事故扩大。我是总设计师,我不仅要为这条艇的安全负责,更要为艇上170多个参试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到底。听了我的决定,艇长说,总师60多岁了,能和我们一道进行深潜试验,那不是夸海口的。
我们的试验进行得很顺利,大家坚守各自岗位,只有艇长下达任务,艇员汇报操作,以及测试人员报告数据的声音。而巨大的海水压力,使艇多处发生了嘎嘎的声音,确实令人毛骨悚然。试验成功了,上浮到100米这个安全深度,艇上的快报要我题几个字。我不是诗人,但也是一时诗兴,题了一首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这个“痴”字和“乐”字,就是我们献身核潜艇的真实写照。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
我们把这四句话归纳为核潜艇精神
问:我们为何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核潜艇这个尖端做成?
黄旭华:我国当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比美苏英法等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大概落后了半个世纪,但在艇的外形、反应堆功率、航速、下潜深度、潜一次能走多长时间等方面,我们的第一条核潜艇比美国的第一条要好。举个例子。美国核潜艇在水下密闭空间能维持多久?他们原计划120天,最后做到83天10小时,我们说它是84天,回来时有几个官兵是用担架抬出来的。我们原想,我们技术没有美国先进,艇员的身体素质也比不上美国人,美国最多是83天10小时,我们能达到80天就不错了。我们是多少?我们真正做到了90天。所以当时我很兴奋,到码头去接他们。船到码头,我们跟艇上通话:“估计你们现在比较困难,为了保证体能、安全靠岸,我们另派一批艇员来接你们,这样安全有保证。”艇上就说:“谢谢你们,我们保证能安全靠岸,不需要你们接。”那个情形确实激动人心,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跑出来,没有一个需要担架。我当时特别高兴,我说:“好啊,我们拿到金牌了!”
总结我们的工作经验,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我们把这四句话归纳为核潜艇精神。中华民族是了不起的民族。只要有坚强的领导,只要下定了决心,要干什么事情,一定能够干成。两弹一星、核潜艇,哪一个不是这样!所以钱学森讲过一句话:“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毛主席讲了一句话:“还可能比人家干得更好!”
退下来后我给自己定位当拉拉队
给他们敲锣打鼓
问:身处核潜艇总设计师这样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岗位,您在管理上有哪些心得?
黄旭华:我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既当所长,又当总设计师,还要当党委书记。那时候实验任务特别重。我的做法是,要抓得起、放得下,大胆放手,让同志们干。我总是把副所长分工好,大胆放手,相信他们,这样我可以大量干我的工作。我不太主张大小事情都是领导一个人干,干不好的。对于技术上的问题,我主张多听同志们争辩,争辩越多越好。
问:从核潜艇总设计师位置上退下来以后,您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
黄旭华:退下来后,我给自己定位是当拉拉队,给他们撑腰,给他们敲锣打鼓,必要的时候可以当场外指导,但不当他们的教练。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忙出出点子,但是一句话,让他们放手去干。
我的父母学完医以后,就在汕尾海丰找了一个最穷最需要医生的地方工作
问:请谈谈父母的言传身教对您的影响?您和女儿们聚少离多,在对她们的教育上又有什么心得?
黄旭华:当年,我的父亲母亲在基督教会办的医院跟英国医生学医,学完后在汕尾海丰找了一个最穷最需要医生的地方工作。他们的医德,老百姓有三句话,叫做爱心、耐心、责任心。
我九个兄弟姐妹,除了最小的一个请了奶妈,其他八个都是母亲拉扯大的。那时我们家房子很小,夏天很热,一到晚上小孩就哭闹。不管怎么哭闹,因为母亲是产科医生,只要有人叫她去接生,她立马就去了。那么多年来,她接生没有出过一次事故。海丰很穷,好多人接生交不起医药费,我母亲老是说,不要想太多,小孩儿会叫人的时候,你抱过来叫我一声干娘就好了。她到底有多少个干儿子干女儿,她自己都不晓得。我们只晓得她一百岁大寿时,来了好多人,有头发白了的,有中年人,问他们都说自己是她的干女儿干儿子。我父亲是另外一种性格,他刚毅,正直,刚强。举个例子,日本人进来,要他帮忙做事,他不同意,日本人拿着军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跪下,他就是不干。
我在工作当中,如果有一点成绩,除了党的教育培养,都是受父亲母亲影响。所以我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毅力。我常常告诫他们,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去闯,不要人家扶。
母亲没有想到,被家人误解为忘记养育自己亲生父母的不孝儿子,原来在为国家做这个事
问:您离家研制核潜艇,才刚刚30岁出头;等到您回家见到亲人,已是60多岁的白发老人。30年中,您和父母的联系只剩下一个海军信箱,这是怎样一种考验?
黄旭华:我从小离家到汕尾中学住校,母亲就把大家叫在一起唱一首歌,叫《再相会》。此后每次离家,母亲都要找大家跟我们唱这首歌。我对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有很深的感情。我离家不是不想家,我经常想家,但我会自己去忍受。我往往想家的时候,就在脑子里暗暗地唱《再相会》。
我母亲再三想了解我在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得到答复,那么长时间母亲也不再问了。当时一方面是出于保密,更重要是工作紧张,所以我父亲和二哥去世时我都没有回去过。妻子再三跟我讲,你必须回去,你不回去会后悔一辈子,家里人也会埋怨你一辈子。好多同志也劝我,你应该向组织上提一提,请个假。我说我向组织上提,组织上一定会同意我回家,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不愿让组织上为难。因此我还是自己承担,自己忍受。
1985年,《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骑鲸蹈海赖神将》,这是中国研制新潜艇第一次见报,当时还没有提核潜艇。我当时意识到,保密的门在放开,应该找机会回趟家了。1986年11月,我到大亚湾核电站出差,回了趟老家。这是我30年后第一次回家。母亲见面后,她再也不问我在干什么了。母亲蛮有修养的,她认为不该问了,也问不出来。
直到1987年,作家祖慰在《文汇月刊》第二期发表长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一位核潜艇总设计师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30年的事迹。我把这期《文汇月刊》寄给母亲,文章全篇没提“黄旭华”三个字,但写了“他的妻子李世英”。她没想到,被家人误解为忘记养育自己亲生父母的不孝儿子,原来是在为国家做这个事。虽然她也相信自己的儿子不可能不要家,但对他三十年不回家难免也有一点埋怨。她蛮激动的,她把子女们找过来,讲了这么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这个事传到我这里,我哭了。我很感谢母亲弟妹们对我的理解。1956年离家时母亲跟我讲,你少小离家,受尽了苦,那时候战乱你回不了家,现在解放了,父母也老了,希望你常回家看看,我是流着泪满口答应的,但是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三十年。我常常想,虽然我没有履行我在父母面前承诺的常回家看看的诺言,但我恪守了保守组织机密的誓言。好多人问我,忠孝不能两全,你是怎么理解的?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母亲最大的孝!
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事业,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问:回过头来看,您如何看待你们当年的付出与牺牲?
黄旭华:1974年我们总结自己的经验,有两句话: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事,一个月38元钱,这样的工资拿了20多年,到改革开放后工资调整了,他们年纪大了退休了。我们刚到葫芦岛的实验基地时,一片荒芜,一年刮两次大风,一次刮半年。一个月只有三两油,最苦的一次半年没有一滴油。我们的伙食主要是苞米面,高粱还算高级品。我们的住地离工厂要爬过一个山坡,大概走50分钟山路。那时葫芦岛的天气是零下20度以下,常常到了深夜,一个电话过来,我们的同志掀开被窝,穿上工作服就走,绝不耽误工作,也没有加班费,根本没这概念。如果在晚上有一杯豆浆,大家就感到心里特别温暖。我们是这样过来的,没有人叫苦叫累。
好多人问我,你们搞尖端、搞创新、搞好多未知的东西,一路历尽沧桑,你们的人生用几个字可以说明吗?我说,我们的人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一个是“痴”,一个是“乐”。痴,是痴迷于核潜艇,献身于核潜艇,无怨无悔;乐,科研生活极为艰苦条件下,我们是乐在其中,苦中有乐,苦中求乐,乐是人生的主旋律。我们是这样过来的。现在回想一下,当年确实艰苦,但当时没人叫苦,工作上有一点成绩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乐在其中。我们核潜艇战线的广大员工,呕心沥血,淡泊名利,隐姓埋名,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还奉献了终身。如果要问,这一生有何感想,我们会自豪地说,这一生没有虚度;再问,你们对此生有何评说,那我们会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事业,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功劳是大家的,荣誉属于集体
问:现在不少人都知道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传奇人生,您如何看待你们所取得的成绩?
黄旭华:我再三讲过,中国的核潜艇是全国大力协同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成员,按照组织分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跟大家一道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而已。功劳是大家的,荣誉属于集体。1974年第一条核潜艇交艇,我们总结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核潜艇精神,这四句话对我们每一位同志都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也有很大的约束作用。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求自己做到的,有三句话:廉洁奉公,勇于创新,敢于担当
问:请您为党员领导干部题写一段寄语。
黄旭华:我写不出来,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努力要求自己做到的,有三句,廉洁奉公,勇于创新,敢于担当。
今年是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怀念这所存在了8年零11个月的大学,清华大学档案馆借此机会公开展出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当时在西南联大时的考卷。八十年过去,大家依然为这份发黄的考卷透出的严谨而折服。除了这份考卷,李政道还有哪些有趣的事儿,且听科学老顽童王渝生一一道来。
李政道也是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30多年前,我还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李政道曾到研究生院作报告。他跟我们说,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读经典、四书五经等,但是我们搞科学的人,可要读另外的三部经,那就是《易经》、《墨经》、《山海经》。
李政道说,《易经》就是讲八卦,八卦就是二进制。当时我坐在第一排,我突然说八卦不是二进制,他听见了,其他的同学也都哄我。李政道问我,“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说我是学数学的”。
“噢”,他说,“那我要听听你的高见,愿闻其详”。
我也不客气,站起来说道,“作为数学中的进制,比如十进制要有十个元素,这十个元素是从小到大的排列,还要有加法、乘法运算。用这些条件衡量的话,八卦就不是二进制,它只有二进制的结构,而且中国古代没有用过二进制。”
他听了之后,点头说,很有道理。
下了课之后,李政道到我身边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王渝生。他说,我今天下午要到中国美术馆去看画展,你能不能陪我去。
哎呀,我求之不得。所以我陪着李政道和他的夫人秦惠君女士,就到了中国美术馆。当时正逢师牛堂主李可染的画展,李可染是专业画牛的。李政道就跟李可染说,能不能通过牛画点科学画?然后,还出了几个题目,比如说正负离子对撞机正在建,你能不能用你的牛画下来?结果李可染听了后,果然画了两头牛在对决。
后来我当中国科技馆馆长的时候,还有幸邀请了李政道来中国科技馆来作报告。他讲得非常生动,说我们科学研究就是一条鱼,科学研究的氛围就是鱼旁边的水,池塘。但是我们研究的成果,一定要拿到市场上去,就像鱼要拿到鱼市卖。所以,科学技术一定要为经济建设,要为生产服务,要用在实际当中去。
李政道的这个观念影响了很多人。后来我曾听很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讲,自己就是听了李政道的报告才走上科学的道路的。
李政道小传
1926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省苏州市。抗战期间曾在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学习。1946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
因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与杨振宁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在物理学领域有很多杰出成就,多次荣获各种奖,至今一直活跃在物理学的前沿。
李政道极力提倡重视基础研究,促成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帮助建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他创办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等多个学术组织,建议设立博士后制度和完善自然科学基金制度,创办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为促进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政道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意大利科学院院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洛克菲勒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中国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名誉博士。
王渝生,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副所长,国际科学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数学会理事暨数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著有《自然科学史导论》《郭守敬》;主编有《数学大师》、《天文太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数学卷》、《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崛起》,主译《跨越大洋两岸的科学文化交流》。发表论文100余篇。曾入选“中国十大科技人物候选人”。2015年7月,王渝生受聘为光明日报科普专家委员会顾问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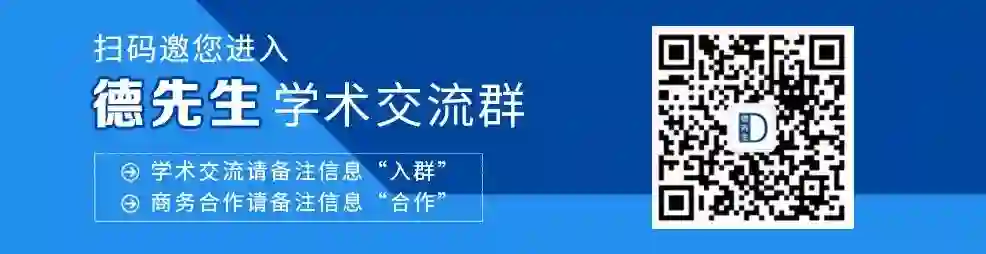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