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德云皇后"的品格


在人堆儿里成了精,又精得不烦人。郭德纲离不开他,德云社的台柱子换了几茬儿,离了谁好像也活了下来,但皇上皇后必须永远不分开。
文 | 卢美慧
编辑 | 金焰
摄影 | 尹夕远
老师挺好
3月初,郭麒麟参加综艺节目《一封家书》,节目组原本想的是,让郭麒麟给父亲郭德纲写封家书表一表两人的父子情。郭麒麟拒绝了,在他心里,父亲“威严”、“庄重”,私下里爷俩都是极内向的人,有些话说不出口,他真的会不好意思,哪怕是写信。最终,他没有像节目中其他嘉宾一样把信写给父母,而是写给了师父于谦。
跟于谦就轻松多了,在信里他可以调笑师父睡觉打呼噜,吃饭永远吃不饱,演出前老是没正形,也可以笔锋一转,想起于谦早年的教诲,“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您说干咱们这行的都是江湖人,既落江湖内,便是薄命人。”还能在最后袒露心迹,笃定又知足地说,“此生得立于门之下,我之幸也。”
这封信把于谦高兴得够呛,当时他正为自己的新片《老师 · 好》跑路演,转场的火车上,他给郭麒麟回信,“我儿诚肯为人,且善良宽厚,踏实做艺,但心高志广。立于皓月之边,不弱星光之势,傍于巨人身侧,不颓好胜之心。”皓月之边,巨人身侧,可以说郭麒麟与郭德纲的父子关系,但对于谦来说,似乎也能看作自身心迹的剖白。
24年的时间,德云社早已巍巍然成为帝国。这个帝国的国王留给外界一个杀伐决断、睚眦必报的印象,作为最亲密的搭档和伙伴,于谦倒真像古时戏文里什么也愁什么也不管的大胖皇后,永远与人为善,永远乐乐呵呵。
人们习惯于站在郭德纲身侧这个大高个儿被换着法儿地挤兑,连同他倒霉的父亲“王老爷子”、“长着护心毛的媳妇阿依土鳖公主”,还有他喜欢漂亮姐姐的儿子“郭小宝”。
于谦永远谦和。不管是台上拖家带口的被揶揄调侃,还是台下十几年德云社经历的历次风波,于谦的态度从来是,不当事儿,不多说,不掺合。
但又不是窝囊,“不弱星光之势”和“不颓好胜之心”也可以拿过来说自己。在相声上,于谦早已被公认为当今捧哏第一人,节奏、尺度、时机、火候恰到好处,妥帖到任谁站在郭德纲旁边都觉得不搭。很多时候,郭德纲甩出包袱静候观众反应,于谦垫上两句,随即全场沸腾。于谦说可能跟很多人对相声的理解不同,很多人觉得相声就要主动出击步步为营,包袱连着包袱可劲儿甩,但于谦说,说了几十年相声,他喜欢那个四两拨千斤的瞬间带来的满足和快乐。在相声世界里,郭德纲是位漫天使活的主儿,但不管怎么飞得没边儿,于谦接得住。
相声之外,德云社一路跌跌撞撞,一地鸡毛的时候有,千夫所指的时候有,漫天飞溅的唾沫星子,身边的人骂街的骂街,站队的站队,杀红眼的杀红眼,于谦真能做到片叶不沾身,乐得逍遥自在。
在人堆儿里成了精,又精得不烦人。郭德纲离不开他,德云社的台柱子换了几茬儿,离了谁好像也活了下来,但皇上皇后必须永远不分开。
郭麒麟刚入行的时候,外界都好奇,这样一位锋芒毕露的父亲,会培养出一个怎样的儿子。时间给出了最好的答案,遍尝江湖辛苦的郭德纲让于谦给儿子当师父,他没教儿子锋芒和争斗之心,反而希望儿子多学学于谦身上的通达和快乐。郭麒麟给于谦的家书发出后,大家都好奇郭德纲的反应,会不会失落?会不会嫉妒?没有,郭德纲转发了儿子的微博,配了一段文字:自有明月照山河。
2011年10月4日北京,于谦、郭麒麟同台讲相声。 图/视觉中国
无心插柳
这个春天,“明月”异常忙碌,相声艺人的身份暂时丢到一边,新片《老师 · 好》中,一直习惯绿叶身份的于谦破天荒当起了男主角,饰演了一位上世纪80年代的人民教师。
藏住身上抽烟、喝酒、烫头的顽固标签,藏住抱着斗牛犬当吉他的摇滚精神,也藏住手攥成小拳头唱《学猫叫》的骚气逼人,收起下垂的法令纹和苹果肌下永远挂着的那个标志性笑容,50岁的于谦这回认真了。
电影中于谦成了学生们的阶级敌人,顽固死板,不近人情,人送外号苗霸天。故事没有多复杂,经历种种误会,学生和老师达成和解,送学生们到达青春的彼岸后,霸天消失于人海,故事也就结束了。
不像学生们那般幸运,苗霸天的青春都给耽误了。手握北大通知书,因为成分不好,最终只能在小地方教书教了一辈子。这一次,于谦认真地演了一个时代弃儿,认真地演了一次求之不得。
故事是一帮人喝酒喝出来的,导演张栾说这主角一定得于谦来演,于谦第一次看本子时死活不肯,但也跟张栾说,爷们儿,你想找谁,范伟老师行吗?韩童生老师行吗?你想找谁,我给你联系。
还真倍儿认真给联系了,但张栾不死心,还是想让于谦演。后来有一天去于谦家里聊天,张栾又把本子拿出来,好说歹说让于谦再看一遍,从凌晨1点开始,于谦戴着眼镜捧着iPad一行一行看,他有喝茶的习惯,张栾就在旁边伺候着,80后的张栾当时也不清楚于谦心里想什么,茶壶烧水的声音咕嘟咕嘟得他都怕吵着于谦,最后给添的都是温温吞吞不怎么热的水。
一直到凌晨4点多,于谦摘了眼镜,放下iPad,沉默了足有5分钟后,他跟张栾说,“你跟王海(于谦经纪人)聊去吧,”说完自个儿进屋睡觉去了。
就这么着,从艺30多年,于谦演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男主角。
起初真没什么人看好这部片子,导演张栾是生面孔,主演除了于谦也没一张熟脸儿,结果却成了3月院线的一匹黑马,上映一周多,票房突破两亿,对于一部小成本电影来说,成绩十分喜人。
抛开网上流传着的各种段子,也抛开郭德纲搭档这个似乎抛不掉的身份,当我们试图审视于谦作为独立个体的生命故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是,在于谦过往的人生片段中,已经不止一次上演过类似无心插柳的故事。
同样的,成为“德云一姐”、“相声皇后”,成为现下公认的最顶尖的捧哏艺人,成为北京最后一代老炮儿的杰出代表,成为中国摇滚协会副会长,好像都是无心插柳的事儿。
这个人从不迫切,但到头来又好像拥有一切。
《老师 · 好》中于谦有句台词,“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这是他完全需要发挥演技的时刻。在于谦的人生中,既没遭逢过贫贱,孤和直更是谈不上,按照时下最烂俗的说法,对照于谦的人生剧本,大约每个人都能立刻成为柠檬精——这个人,命可真是太好了。
电影《老师 · 好》剧照。 图/网络
宠儿
于谦这辈子受过的委屈大约都在相声舞台上。真实人生里,于谦的故事实在太没有波澜,书写人物的那套范式在他这里近乎失灵。他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坎坷,没有什么决定命运的转折,没有必须要完成的梦想,苗霸天那种被命运伏击的悲剧,那种心心念念,那种求之不得,在他这里,统统没有发生过。
为中国相声事业作出卓绝贡献的于谦的父亲母亲都是石油系统的高级知识分子,年轻时工作忙,儿时的于谦跟着姥姥和5个姨妈长大,换言之,他打小儿是在泛滥的宠爱中长大的。
记者采访这天,坐在德云会馆富丽堂皇的会客室内,50岁的于谦回忆起儿时趣事,还会故意挑挑眉毛,一脸你们没赶上的得意。
他出生于1969年,计划经济时代长大的孩子,乐趣都要自己去寻找,于谦找的是自然。于谦很兴奋地说起小时候的自由,一大家子人都宠着他,又因为父母不在身边,于谦也就没有经历中国传统家庭对一个孩子的驯化和改造。他有大把的时间去释放天性,也不必担忧什么不可抗力把他的天性修剪掉,那是真的广阔天地为所欲为。有阵子迷上养鸽子,姥姥就腾出半个厨房给他折腾。喜欢养鸟,就天天泡在鸟市,跟着全北京最逍遥的养鸟人,打听背后的门道儿。
父母都是那个年代国家的栋梁,但于谦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可能不是当栋梁的料,“小时候我就想啊,我选择一个我喜爱的工作,这一生多幸福啊,我何必非要苦啦吧叽地不喜欢科学家,还非得当科学家去,当了科学家我还不一定能干好,而且我还不痛快,这何必呢?”
相比于父亲,小时候的于谦其实更怕妈妈,妈妈不打人,也不骂人,但眼神语气中大约还是有他能长大成材的愿望,而且记忆力超强,一件事两年前提过,两年后突然想起来,就再念叨一遍,老也过不去。
这是童年时代唯一能记起来的一点不快乐,不过所有不快乐都有期限,父母工作很忙,通常一年只能见两三次,最多不超过4次。
打小长在北京胡同的大杂院里,于谦性格里有老北京人天然的温厚和亲和。更重要的是,姥姥和姨妈们的宠爱,并没让于谦变成多么纨绔的孩子。
于谦的二姨是老师,小时候他就在二姨班上上课,这次电影很多时候于谦就照着二姨的样子去演。他记得那时候班上有个女同学患小儿麻痹症,不只行动不便,智力也受了一些影响,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于谦每天就看着二姨照顾那位女同学。上学时他们两个一起出门,于谦坐公交车,二姨得骑自行车,公交车到站后于谦在车站等,然后远远地看着二姨驮着那位女同学走近,3个人再一起进校门。上完课之后,所有同学都走了,二姨把于谦和那位女同学留下,给女同学补作业、讲课,于谦就在边上瞅着,一遍讲不明白,再讲一遍,听得于谦都烦了,二姨还在耐心讲,直到讲明白为止,然后再像上学时一样,送女孩儿回家,整个小学,于谦都是这么过的。
受尽宠爱,又在幼年耳闻亲见了人间真正的善良,这样的人格教育让于谦受用一生。采访中不可避免地被问到自己和郭德纲性格的不同,于谦说起当年侯耀文评价郭德纲的话,“郭老师一路坎坷走来,势必嫉恶如仇。”而他自己,命里真没这些东西,“那些恶的、丑的,我真的没有概念,所以就一切善待,对所有的事物、人物都是。”
殊途
有了自由和善良的基石,于谦接下来的人生故事便都顺理成章了。
粉丝们做过一种假设,如果德云社没有成功,郭德纲就是满腔抱负不得伸展,必然万千郁结在心,日子没法儿往下过,因为他爱相声。
于谦呢,如果德云社没有成功,他该吃吃该喝喝,估计会在别处找到快活。他也爱相声,但大千世界,乐子有很多,日子总能往下过。
两人相识之前,同处相声行业的冰河时代,两个爱相声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郭德纲只身北漂,带着一身本事不知路在何方,最穷的时候要把小灵通卖掉换馒头吃,演出完没赶上公交车一个人走20公里路回大兴的出租屋,边走边哭,但即便这样,他有信念,再怎么吃苦,再怎么被侮辱,相声必须说下去。
于谦这边,姨妈们陆续成家,姥姥年纪大了,就被姨妈们接去住,于是房子只有他自己住。他爱交朋友,玩儿心极重,相声最不好的那几年,他的生活是:
那段时间我们可算玩儿疯了,从春天水面一解冻就开始忙活钓鱼,每天不是水库就是鱼坑,只要听说哪儿的上鱼率高,抬脚就走,绝不犹豫。这样玩儿到10月底,大风一起,钓鱼暂停,进山逮鸟,拿着工具,带着帐篷,我们在山里一住就是半个多月,直到候鸟迁徙完毕,才回家休整,重新装备,进入水库区去捞虾米,一玩儿又是一个星期。那时的车里就像个百宝箱,鱼竿、鸟网、虾米篓、调料、碗筷、煤气罐,应有尽有。走到哪儿,就地取材,随遇而安,大有野外生存训练的意思。直到天气大冷,水面封冻,我们这才回到家里,重新开始养鱼驯鸟,吃吃喝喝的生活。
偶尔饭桌上喝点儿酒之后也会想起相声这茬儿,就让媳妇儿拿一小DV在旁边录,他跟朋友说上一段解解馋。这个情节后来被很多人当作于谦相声生涯中的一段黑暗时期,这次采访又被问了一遍,于谦哈哈大笑,“这就是爱好,我没伤心,我只是灰心,我可能不会以这个为谋生手段了,那还有别的啊。你们觉得惨是吗?没有啊,当初就是觉得好玩儿,说完了我们继续喝酒去了。”
于谦从不是那种大任在肩的人,天塌下来谁爱顶着谁顶着,跟他没关系。“所以对相声,喜欢是喜欢的,但是一直没有说那种,就是相声死了怎么办呀,我得帮它怎么——”这句话没说完,于谦赶紧把话茬儿接了过去,双手扶着椅子背儿,一脸豁达地说,“它死了就死了呗,跟我又没什么关系,对,我对相声没有责任,它不欠我什么,我也不欠它什么。”
玩家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就都熟悉了。
2000年,于谦与郭德纲相识,至少在于谦这里,最开始的合作只是因为舒坦,好玩儿,却没想到这偶然的缘分,在之后的岁月里,缔造了中国曲艺史上的一段传奇。
对郭德纲来说,这是一段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混合着梦想、屈辱、荣耀、复仇和泪水的个人奋斗史。但对于谦,就是挣得比过去多了,时间比过去少了,以及全国人民都知道他的爱好是抽烟、喝酒和烫头了。
不管是早期李菁、何云伟、曹云金等人的出走,还是后来主流相声界的围攻,或是之后郭德纲跟北京台漫长的口水官司,以及去年沸沸扬扬的家谱风波,郭德纲的确如侯耀文预言的一样,他不愿意大度,绝不原谅不想原谅之人,偶尔还会透出江湖事江湖了的狠辣。每一次风波,大家都好奇皓月之边、巨人之侧的于谦会怎么做,结果每一次,于谦什么都不做。
莫说风波之中,即使表面上风平浪静的时候,于谦也不掺合。一个反复被早期德云社粉丝回味的细节是,2009年封箱演出,当时还没有后来的出走风波,台上8个人说了一个名为《到底是谁》的群口相声,情节是德云社要评选优秀员工,有巨额奖金。站在台上郭德纲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在德云社,让你挣多少钱,你才能不走?众人插科打诨嘻嘻哈哈都糊弄了过去,轮到于谦,他的反应是,“这个,我不参评吧?”郭德纲现甩包袱,“你是礼仪小姐。”于谦接住,“是什么都没关系,我先躲开这题吧!”
于谦与郭德纲缔造了中国曲艺史上的一段传奇。 图/ 视觉中国
身处风暴中心,于谦每次都做到了片叶不沾身。争来争去说到底不外名利两个字,恰好这两字,在于谦的字典里实在没什么优先级。
大家伙儿忙着撕逼吵架的空档,于谦捧着手机在演出间隙追忆起自己的似水年华。2013年,于谦把手机里积攒的十几万字集结成书,取名《玩儿》,书里他养猫、驯鸟儿、养鸽子、偷鱼、熬鹰、喂马,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没有他不爱的,没有他不玩的。
作为多年搭档,郭德纲给自己的“皇后”亲自写了序言:
和于谦师哥相识十余载,合作极其愉快。台上水乳交融,台下互敬互重。抛开专业,谦哥在“玩”之一字上堪称大家……
接触十几年了,我对谦哥甚为了解。他不争名,不夺利,好开玩笑,好交朋友。在他心中,玩儿比天大!
这则序言的题目是,《他活得比我值》。
书的封面用的是漫画,一个立于墙边的人身着长衫,头顶草帽,提笼架鸟,旁边的围墙一树繁花,花朵中间有一行小字,“我就这么点儿梦想。”
记者此次采访中也问了梦想的话题,被问到小时候的梦想,于谦在座位中挺了挺腰杆说,“动物饲养员。”这话一出整屋子的人都乐了。但于谦答得很认真,一连强调了3遍“真的”,“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小时候我就想着,我有朝一日要能上动物园养动物就好了。”
自由,自在
于谦没去动物园养动物,他给自己开了个动物园。
人生中大部分事情都是无心插柳,只有对动物的喜欢,于谦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很多的精力,还有大笔的钱财。
张栾记得有年夏天大家去于谦的动物园聚会,天气热得要命,大家伙儿都在空调屋里喝着茶,聊着天,“他就在外面转着,就在那个小马那马圈里面,一会儿逗逗那个鸽子,一会儿去轰鸽子,就那么大太阳地儿在外面转一天,不进屋。”
没有真爱之外的其他解释,尽管时间已经拖拽着他进入了50岁,但提到动物的时候,于谦脸上依然布满孩童般的天真,他把这个归结为天性,从小就喜欢,这份喜欢又非常幸运地没有被阻遏和中断。
于谦给马场取名“天精地华宠物乐园”。 图/ 视觉中国
小的时候,胡同里的大人们有一整套编排于谦的词儿:打鱼摸虾,耽误庄稼;年纪轻轻,玩物丧志;提笼架鸟,不务正业;八旗子弟,少爷秧子;清朝遗风,未老先衰。
但说的时候大人们都一脸和善,于谦自己也当好话儿来听。他自己心里也有数儿,说是八旗遗风,他对王孙贵胄的人生天然缺乏兴趣,年轻时听上了岁数的养鹰人讲清朝贵族打猎的事儿,这话让别人听大概就是贵族生活多么潇洒惬意,但于谦心思都在动物身上,他在《玩儿》里写过这段心事:
这一段聊天听得我心神俱醉,如梦如痴,仿佛穿越到了清朝,一同跟随皇帝出围打猎去了一样。不过如果真有此事,我也绝不变身为王公大臣、龙子龙孙,我宁可身为一个把式伙计,天天陪伴在我喜爱的动物身旁。
于谦身上最让张栾佩服的就是这股纯真,两人喝酒的时候聊过,好多人会说于谦是有了钱才能这么玩,于谦很认真地跟张栾说,“我要有钱我真就没事我就玩儿游艇去了,我养游艇,我天天跟人家打高尔夫,全国各地找好场地。你看我玩儿这个,还是过去市井玩儿那些东西,还是那种生活中的情调的东西,真的跟有钱没钱没关系。”张栾也是北京孩子,他的理解是,在于谦身上,就是胡同里那个喜欢养小鸟养鸽子的小男孩长大了,他长大了还是喜欢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在胡同里长大的北京孩子,有了钱之后他还是一个在胡同里长大的北京孩子。”
相比名和利,因为玩儿聚到一起的友谊要简单纯粹得多。
胡军因为马和酒跟于谦玩儿到了一起,“轻松,没负担,干净。”胡军这么评价跟于谦的友谊,喜欢马的人身上都有江湖气,不是勾心斗角、人心险恶的那个江湖,而是“豪情仍在痴痴地笑”的那个江湖,这一点上,两人浪漫到了一块儿。
音乐人栾树和于谦打破了相声和摇滚乐次元壁的友谊也是因为马。栾树从1989年就开始养马,经历过中国摇滚从灿烂转向清寂的整个过程,栾树觉得,马的世界有种持久的纯净。第一次见面于谦到栾树的马场找他,两人一见如故,门外支张小桌儿,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从下午聊到凌晨,“我们就想把相见恨晚的那些年都补回来,一直聊一直聊。”
外界都好奇搞摇滚的怎么会跟说相声的玩儿到一起,栾树说其实特别好解释,摇滚乐最核心的精神是4个字,“自由,自在”,“其实相声也是,人在笑的时候,也是自由和自在,是共通的。”
老话说,人生四十不交友,结果两个人都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碰到了自己的知音。因为这段缘分,才有了后来栾树个人作品音乐会上,于谦一身闪亮的铆钉印花牛仔服,扯着嗓子跟栾树合唱《怎么办》的那段灵魂表演。
于谦当天在台上放松极了,宛若自己主场,栾树在边上一边唱着一边笑着看,回想当时,栾树觉得那是自己人生中最美妙的表演之一,好兄弟在身边,大家一起唱自己写的歌,唱到呼哧带喘还是很开心地唱,太快乐了。
人群中
于谦是个在人群中长大的人,所以他永远离不开人群的热闹。他必须热闹,必须有酒有肉有朋友,乔杉跟于谦在《缝纫机乐队》中认识,“一下去就喝,喝出了革命友情。”
拍戏中间喝点儿解馋,拍完了可以敞开喝,有回拍戏拍到凌晨3点多,于谦和乔杉叫上以前连宵夜也不吃的韩童生,从凌晨3点一直喝到早上7点,喝了有2斤白酒,“韩老师讲他们团的事,谦儿哥讲他们团的事,哎哟,热闹极了,听着他俩在那儿说有意思。”
喝了那么多次酒,乔杉印象中从来没有跟于谦唠过什么灵魂嗑儿,思索人生的意义啥的,都没有,都是开心的事。喜剧演员私下里大都会有忧伤的一面,乔杉就会,他看不了夕阳,每次一看别人说好美,他都觉得很残忍。但是类似的心情于谦从来没有,“你看不到他不快乐的时候,连一个瞬间都看不到。”
别人是借酒消愁,半醉半醒的时候跟大伙儿说人间不值得。在于谦这里,人间太值得了,他喝酒时无愁可消,要的是那个不负人间一场醉的快活。拍戏的时候有一次在昆明转机,早晨9点多到机场,于谦跟张栾说,咱找地儿喝点吧。大清早的,咖啡店也没酒卖,最后在贩卖机小卖店之类的地方码了几罐啤酒,美美地喝了那么一会儿。张栾印象中于谦喝酒那真是随时随地,一秒入戏,但酒品很好,真喝多了就绵绵地在那儿一坐,笑眯眯地看着大伙儿,活脱一尊佛。
还有一回张栾在洛杉矶拍戏,正好赶上于谦也到洛杉矶,当时于谦正在戒酒期,十分艰难地坚持了两个月有余。结果一帮人凑到一起,于谦说,哎呀,你好久没吃中餐了吧,我洛杉矶有朋友开餐馆,一起去吃。
一堆人坐下,发现桌上没酒,这个时候于谦身边的王海开始翻手机,“翻着翻着,海哥就说,哎呀,今天我这媳妇她那个三舅的什么什么去世了,这发朋友圈了。其实特远一亲戚,结果于老师说那咱们得吊唁吊唁啊,寄托一下哀思,不如喝杯酒吧。”
这样的脾气秉性自然让于谦交遍了天下的朋友。他予人真诚和快乐,对方也毫不吝惜各自的真心。歌手景冈山跟于谦认识了二十几年,他对于谦最大的印象就是人如其名,然后这谦和的性格又帮他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次《老师 · 好》的客串名单排了密密麻麻的一页,连从影视圈消声匿迹许久的马未都都露了一把脸,说起来马未都上一次跟影视圈发生关系还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那时候身边还是王朔、赵宝刚那批人。这次之所以出山也是因为马,“我们在一起就很快乐,于谦是一个很温和(的人),让人舒服,这很重要。”马未都知道自己不会演戏,但还是愿意过来帮这个忙,气味相投的人凑到一起就有乐子,大家就老想往一块儿凑。
有时候你都弄不清楚于谦这些朋友是什么时候攒下的,何冰、杨立新、刘威、张国立等等等等。吴京当时身上有伤,是拄着拐杖到的片场,下车的时候剧组甚至安排了轮椅,结果于谦只给了一场戏,急得吴京追着他喊“谦儿哥你都把我弄来了,你不多用用,这是糟蹋东西。”于谦也是这部电影的监制,每个过来的朋友剧组都给封了红包,多少是那么个意思,张国立走的时候连吼带喊,死活也不肯要,这边就追着非要给,张国立车开动了,这边从车窗里把钱扔进去,结果车开到门口,钱又从车窗给扔了出来。
乔杉觉得于谦身上最大的魅力就是有“人味儿”。“好像在这个行业里面,大家越来越标准,你见过那种没人味儿的对吧?”乔杉说,跟于谦在一起不会,演员就是一个职业,大家下了班一起喝酒吹牛逼的革命战友,喝得飘飘乎的时候,就觉得在这堆人里不用伪装,不用面具,什么都不用想,那感觉“特松弛,特自在,特美,特值”。
郭麒麟为于谦的电影路演站台。 图/ 视觉中国
绝配
喝酒也喝出过乱子,最绝的一次是2011年在北展剧场表演《汾河湾》。那回适逢于谦再次戒酒3个月,时间一到,于谦跟朋友们凑到一起敞开喝了一大顿,结果直到演出前才被拉到现场。一路上于谦都不省人事,小辈们又是灌水又是催吐好不容易给弄上了场,结果上台之后于谦全凭意识流捧哏,逼得郭德纲在台上使出十八般武艺,最后甚至还翻了筋斗。
因为这段插曲,这场《汾河湾》成了粉丝们心中意外的经典,网上说这是德云社相声最严重的车祸现场,也因为于谦喝醉的事儿,这个版本又称“贵妃醉酒版《汾河湾》”。
很多年以后,长大成人的郭麒麟重说《汾河湾》,还不忘拿这茬儿跟搭档阎鹤祥砸挂,这边阎鹤祥嘴里一捣蒜,郭麒麟赶紧接过来说,“想起了当年我爸被我师父支配的恐惧。”
郭德纲说观众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每当《太平歌词》唱到动情时,甚至能看到他眼里有泪光闪动。观众给了他声名地位,也给了他尊严和安全感,因为喝大酒把观众晾一边儿,于谦自知冒犯,这件事以他凌晨3点多酒醒后给郭德纲打电话道歉结束。从那以后,向来散淡的于谦才给自己立了演出前不喝酒的规矩。
郭德纲不爱热闹,朋友很少。德云社每年有大量的外出巡演,演出合同里一定会写明一条,不和除演职人员以外的人吃饭。一路江湖风雨,落魄时没怎么受过他人恩惠,碰到的都是人性寒凉,现如今就更不需要太多朋友了。
但是对一路相伴而来的于谦,郭德纲这些年越来越愿意释放自己的细腻和柔情。每年生日哥俩儿都有在微博对诗的习惯,今年郭德纲写的是“半百光阴人未老,吃喝抽烫志犹坚。五十华诞开北海,三千朱履庆南山。”于谦和的是,“自幼幸得承祖艺,至今尚未谢师恩。又蒙我角多错爱,天命犹思报德云!”让于谦惊喜的是,今年生日,郭德纲夫妇托了好多朋友,给他送来了一匹血统很是珍贵的名马。
早些年于谦接受采访,说自己和郭德纲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几经风雨之后,这关系里沉淀出许多让人动容的情分。这对气性品格、人生志趣迥然不同的搭档,合作已经快20年,这20年也是中国相声从濒死边缘到重新焕发生机的20年,从一门老手艺的传承发扬来讲,两个人的贡献怎么赞美也不过分。20年中,于谦把不争不抢的品格贯彻始终,到头来收获的,远比去争去抢得来的多得多,比如一个性情寒凉之人,瞒着他给他买马的一份真心。
马未都从十几年前小剧场时期就听两人的相声,他认为这是一对天造地设的搭档,“两个人是一个互补,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互相不去强求对方。”在他看来,这种互补是相声的福气,因为大家心思都在相声上,让关系变得非常简单和纯粹。
两个郭德纲成不了事,两个于谦更不可能。按照票友们的说法,中国相声这门技艺没死绝,真要感激祖师爷在天有灵给下边儿安排了个郭德纲,也得亏祖师爷显灵的时候给郭德纲配了个于谦,换其他任何人,绝无可能。
这是命运的神奇之处。关于父亲和师父的不同,大约没有人比郭麒麟更有发言权,“我特别想纠正大家一个错误的观点,郭老师本性也是一个很温和、很谦和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迫于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才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他都这样还有人欺负他,他再温柔那更活不了了。”
马未都觉得郭德纲的性格很像王朔,私下里都很内向脆弱,“你看他们攻击别人,但准确地说他们这种人格叫反攻击性,他并不是主动地去攻击别人,他就是反抗特别强烈。他一旦被人家给搞一下子,他的反应一定比普通人强烈。”这样强烈的人旁边有于谦的圆融开阔做中和,实在再合适不过。
少年老成的郭麒麟觉得,“在外界来看,这郭老师是一个内向的人,于老师是一个外向的人。在我看来透过表面,两个人的区别其实不是很大,因为你要知道,要好的两个人身上肯定会有很契合的地方。”
这个很契合的东西是什么,郭麒麟也形容不出来,就像从小在两人身边长大,父亲严肃、沉郁,或者外界说的小心眼儿,想不开,但他一直觉得父亲是个非常乐观的人,一定有个特别积极的东西牵引着他,要不他绝对不能坚持到现在,早被压垮了。同样的,人人都说师父快乐似神仙,逍遥没烦恼,但郭麒麟总觉得,于谦活泼热闹的表象之下,骨子里可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悲观,所以才会把每一天活得那么彻底。
于谦在北展剧场后台。图 /视觉中国
一点点悲观
这一点点的悲观是什么,于谦和他的朋友们都没给出答案。其实于谦也不是没有烦恼,儿子转眼就要到青春期,这个在相声后台长大的小机灵鬼儿没有按照于谦的想法长成他想让他成为的样子,所以有时候免不了着急上火。最开始张罗动物园的时候,于谦的想法特单纯,就是想让孩子能多接触接触自然,多接触接触动物,可儿子慢慢长大,对于父亲为他所做的一切“完全不感兴趣”。
整个采访下来,于谦只有在此处皱起了眉头。但是很快,他又疏解自己,生命这东西,强求不得。于谦很有一套消解烦恼的方法,很快他开心地说起,儿子的数学很好,不用学都很好,这让于谦觉得生命真是玄妙,父亲母亲没把他培养成科学家,科学家的基因封存了一代,又在下一辈儿人身上凸显了出来,这样也挺好。
万事不强求的个性和高效的烦恼消化能力,始终让于谦拥有一份轻盈,他从来不会把人生看得过于沉重,任何烦恼都不会真正绑架到他。
更准确地定义于谦的那一点点悲观,应该是老庄哲学里的那一点不那么积极的自由。于谦不想当王公贵胄,太累了,远不如跟动物在一起舒坦。相声里更多人喜欢逗哏,挤兑人琢磨人多有意思,人人都喜欢当千斤,他偏喜欢那个四两。他没有当主角的心,甚至这些年好多人追着他给他钱当导演,他不干,自个儿又懒耳根子又软,对控制别人更是没兴趣,他知道他干不了,统统都拒绝了。
《老师 · 好》中安排了于谦的老年戏份,那天化妆化了好久,从车上下来的瞬间,张栾的眼泪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就是你心里说,他不能老,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儿。”
电影《老师 · 好》剧照。 图/ 视觉中国
倒是于谦还老顽童似的逗大家玩,故意做出哆哆嗦嗦的老迈样子。后来剪片子的时候,张栾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大家都说于老师多么快乐,其实这些人世间的悲哀痛苦,他心里一直明白,“他肯定是明白,只是从来不说,不明白他演不出来。”
于谦可不愿意想悲哀啊痛苦啊这些吓死人的形而上的命题。倒是他费尽心血写的那本《玩儿》里,有一个章节是,《玩意儿终须落声“嗨”》,意思是说你再怎么珍惜的玩意儿最终命运都逃不过“死、走、逃、亡、毁”5个字,最终剩的,只有“嗨”的一声叹息。
但这一声“嗨”的结局,绝对不会耽误他去追求和享受过程的美妙。网友们对《玩儿》的评价是,“文笔幼稚,感情真挚。”于谦让大家相信,就算有一天他真的老了,老到躺在病床上,你跟他说偷鱼逮鸟的事儿,他也能一边吸着氧一边快活得跟你聊到天亮。
采访中他还主动说起了油腻的话题,“就你们说的油腻中年老男人,我觉得我挺油腻的。你要觉得我不油腻是因为我今天出门洗澡了。我自己心里明白,我是一个特别世俗的人。世俗在我这里不是贬义词,最起码它能让你在这个世上活得不那么辛苦,游刃有余。”
于谦一直享受着当个俗人的快乐,享受着当个俗人的松弛,也享受着当个俗人的放肆和得过且过。记者采访开始前,见面后还没完全落座,于谦先招呼助理拿来随身携带的药盒儿,红的蓝的白的药丸好几种,治血压高的,治糖尿病的,里面还加了几粒保健药,一把塞进嘴里才开始正题。后来聊到喝酒的事,问他:“您都吃那么些药了还喝啊?”于谦抬起头,脖子像安了弹簧似的摆了一摆,脸上憋着坏笑,语气跟台上说相声没有两样,“吃药是为了干什么啊,啊?不就是为了能好好喝酒吗!”

每人互动
于谦身上令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推荐阅读
(点击图片即可获取全文)



文章授权转载自人物(ID:renwumag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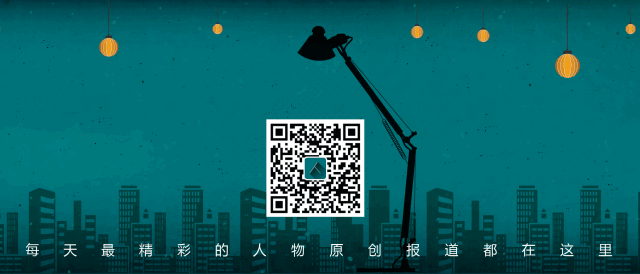
点击
阅读原文
查看更多历史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