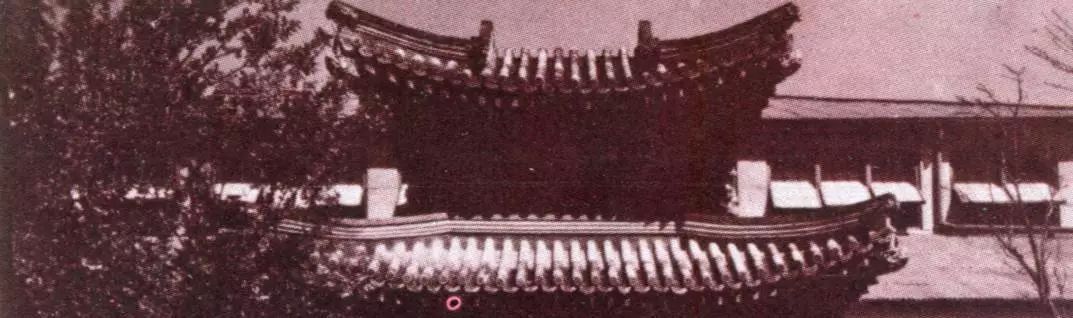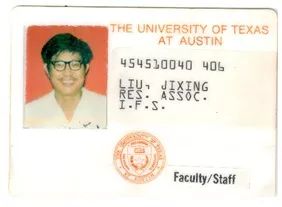周末大家谈—刘寄星 (连载III)
本期嘉宾: 刘寄星 文字整理: 王进萍
刘寄星,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等离子体理论和生物膜形状的液晶模型理论研究。曾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物理名词委员会委员及副主任,参与《物理名词》第三版的修订;担任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物理学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及科学出版社“现代物理学基础丛书”编委会委员,促进国内物理学著作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物理学》编委,撰写“非线性科学”有关词条;与人合译朗道、栗弗席兹《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七卷、第八卷;与人合编文集《木铎金声集》与《挑灯看剑集》;历时八年,主持翻译物理学史三卷巨著《20世纪物理学》;长期担任《物理》杂志副主编,为促进国内物理学及物理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4年与彭桓武(左一)、庆承瑞(左二)先生合影
(1)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78—1980)
1978年9月,我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事处报到,和导师陈春先见了一面。他知道我是1964年的研究生,此次重新考研,不过是想改换门庭而已。他也知道我在考试前已和与他一个研究室工作的庆承瑞老师说好,我到所后和她一起工作。庆承瑞是何祚庥的夫人,原来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学的老师,在莫斯科大学留学时与陈春先熟识,后来调到物理所从事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因我是学生身份,除与庆先生合作研究外,还必须到设在林学院的科学院研究生院上课。记得我在研究生院选了彭桓武先生讲的《理论物理导论》,李政道讲的《统计物理》,还花了不少时间练习英语口语。那时李佩老师担任英语教研室主任,从国外请来了外籍教员 van der Water 和Lindel两位女士教口语,对于我们提高英语水平帮助很大。1979年庆承瑞先生转到新成立的理论物理所工作,我也就成了理论物理所的研究生,跟着她做核物质的统计物理研究。
1980年春节后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工作,突然有人通知我说何祚庥副所长请我去见他。到了当时理论物理所小院简陋的接待室,见何先生和一位外宾坐在那里,小黑板上写着我的名字。何向外宾介绍我之后,就出去了,留下我与外宾交谈。这位外宾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先询问了我的学习经历,学过什么课程,做过什么研究工作等等。之后他说对我的回答很满意,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学校学习。我当时已经42岁,有两个儿子,来理论物理所当研究生不过是想换个工作环境,哪里还会奢望出国。出于礼貌,我说我当然很愿意出去学习,不过鉴于我已经结婚生子,必须与夫人商量后才可以作决定。他拿出一套申请表格,告诉我如果决定后愿意来,将表填好后寄回得克萨斯大学,他们即可接受我为研究生。
回家经过商量,得到夫人支持,父母也支持我出去学习。填表寄出几个月后,收到克萨斯大学发来的录取信,答应学习期间给我一定经济资助,要求于1980年秋季学期入学。
当时科学院对出国留学抱鼓励支持的态度,很快给我们办了护照,并以公派出国的标准发了置装费,那时候我的月工资是56元,置装费一下发了780元,比我一年的工资还多。当时中美之间还没有直接通航,1980年8月我们一行约20人从北京出发,先坐中国民航经飞卡拉奇、德黑兰到巴黎,再从巴黎乘法航到华盛顿。记得在德黑兰机场过境时,曾被伊朗的“革命派学生”要求在霍梅尼像下合影。我们因飞机晚点,在巴黎停留了一天一夜,期间我们8个研究生曾不顾中国驻法使馆“不许离开机场”的规定,从此行负责人李爱珍同志(赴美作访问学者的科学院上海硅酸盐所的一位女同志,因回国后作出很大成绩被美国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但没有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手里领到发给每人的3美元行李费,坐火车去巴黎近郊的街道看了一眼,也算是第一次领略了西方世界的景色。
(2)留学美国(1980—1986)
到华盛顿后,我们在中国大使馆待了约一周时间,先是柴泽民大使和夫人接见我们,鼓励大家努力学习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美国科学工作者交朋友、增进民间友谊。他一讲话我就听出是山西人,会后问他果然是,说“很荣幸”认识我这个小老乡。之后由使馆教育处的同志介绍美国情况和有关注意事项。记得使馆教育处处长是原北京团市委的,对我们很热情。根据美国各个地区的物价指数,使馆发给大家每人半年的生活费,我去的得克萨斯州最便宜,标准为每月400美元(我们得到校方资助后,将多余款项退回了大使馆)。之后,我们就各奔东西,分别到各自的学校,与我一起去得克萨斯大学的是科学院高能所的李先卉同学。
1980年8月赴美留学时全家在机场合影(左起次子刘志、刘寄星、长子刘毅、夫人王淑坤)
得克萨斯大学(UT)的主校校园位于德州首府奥斯汀,是一座很美丽的大学城,当时人口30万。到奥斯汀后我们受到香港同学会的热情帮助,尤其是物理系的邓囤生同学积极帮助找住处,介绍系里情况,使我们很感动。当时得克萨斯大学只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十来个访问学者,我们是第一批研究生。
9月学校开学,物理系一共来了4位大陆留学生,除李先卉和我之外,之后来的还有复旦大学孙煜峰和理论物理所张天蓉(张是物理系女教授Cicielle De-Witt为报当年彭桓武先生将她领入物理之门的大恩,专门从理论物理所要来的一位女学生,比我们晚到了一个多月)。
得克萨斯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必修课程有7门,他们称为“big seven”,其实就是我们的“四大力学”加《数学物理方法》,不过他们将量子力学和电动力学各拆成2门课,就成了7门课,课程内容比国内的四大力学要深。必修课修完后,必须作一篇论文,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才可以作博士论文。为了快些毕业,我第一学期选了《数理方法》、《电动力学I》和《统计物理》3门课,系里负责研究生事务的教授(graduate advisor)Gleeson提醒我说,他还没有见过一学期选3门必修课的学生,建议我减掉一门。我说让我试一试,实在不行再减。上课以后,觉得负担果然不轻,每门课都要做很多习题,还有各种小测验。不过我觉得还可以应付,期末考试后三门课都得到最高的分数“A+”。除了上课外,系里给我们的资助是做所谓grader,即为某位教授的低年级课程改学生的习题和考试卷子,每个月可以挣350美元。这份工作的工作量也不小,因为低年级的物理课面向全校学生,有时候选课学生达一、二百人,美国教授教这种课程不太负责,一堂课后给学生布置许多习题,学生每周交来的习题很多,改起来相当费时间。
由于西方长期对我国进行封锁和不实宣传,一开始美国的教职员和学生对我们这些“红色中国”来的人既生疏又好奇,经过一个学期的交往之后,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赢得了声誉。教我《电动力学I》的Horton教授因为我期中、期末考试成绩每次都比最好的美国学生高出20几分,接近满分,在第二学期专门找我谈话,问我在哪里受的教育,当我告诉他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时,他对“红色中国”的教育水平感到很诧异,邀请我给他做研究助理,答应我每月给500美元。我因已与系里签了做grader的合同,故答应他从暑期开始做研究助理,他对我为什么不退掉350美元的工作去挣500美元很不理解。
为我们讲《数学物理方法》的教授Philip Candelas,因为我在他的期末考试中解出了他认为谁也解不出来的一道数学题与我成了好朋友。他曾问我是从哪里学来的办法,我告诉他是从北京大学王竹溪、郭敦仁合著的《特殊函数导论》书上学来的,他也感到惊奇。Candelas是西班牙裔英国人,与大名鼎鼎的的Hawking都是剑桥大学Sciama教授的学生。他对我们几个中国学生特别友好,经常邀请我们去参加聚会(Candelas后来被选为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接替Penrose的职位担任牛津大学数学研究所席位教授)。通过他我又认识了有名的广义相对论专家Schild教授的遗孀Winnie Schield女士,Winnie出生于加拿大,从小听父亲讲过中国的古文明,十分关心中国的现状并热心为我们提供各种帮助。她是学习英国文学的,在得克萨斯大学学生咨询中心工作,后来她曾帮助我润色过博士论文的英文,可惜4年前去世了。
2003年刘寄星赴伦敦出席IUPAP召开的“科学不端行为以及物理学刊物在防止与调查此类行为中的作用研讨会”时在牛津大学数学所与Philip Candelas的合影
我们与美国学生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同期入学的Darrell Gritz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毕业于美国维尔吉尼亚军事工程学院,曾因反对越战而被派到越南作战,承担最危险的战地背报话机的任务。他大学毕业后已是一位很能干的机械工程师,但为了解决未来的能源问题,辞掉了原来的工作来做研究生,想学等离子体从事核聚变工程。美国学生一般数学不好,连三角函数的和角公式也要查手册,Darrell也是如此。我常帮他解决学习中的困难,因而逐渐熟识起来。他曾在寒假期间开车带我去密苏里州Springfield市他的父母家里过圣诞节,并带我去圣路易斯市附近的密苏里河看马克.吐温当年乘坐过的汽船。
系秘书Janie Trebichevsky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她的办公室与一年级研究生的大办公室对门,我们几个中国人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在办公室做作业或改卷子,有时她很晚来系里加班我们仍然在,感到好奇,常与我交谈。通过交谈,得知她的丈夫是朝鲜战争期间阵亡的美国飞行员,但她并不恨中国人,反而很佩服中国人的勇敢精神。我们到系里一个月后的一天,她悄悄告诉我说“FBI的人来调查你们了,问我你们在系里干些什么?我告诉他们你们每天都在我对门的办公室学习”。在UT的5年中,得到过Janie女士的许多帮助。与这些美国友人的交往,大大提高了我们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也使得我们的学习工作环境大为改善。
通过三学期的努力,我学完了所有的必修课,所有课程的成绩都是A+,学校留学生办公室副主任在我去取成绩单时曾表示,她没有见过有别的学生取得过这么高的学分。
做完两学期的grader之后,我开始在得克萨斯大学聚变研究所(Institute for Fusion Studies,IFS)作Horton的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 RA)。该所由美国能源部资助,研究所的举办权是得克萨斯大学与MIT、Princeton和威斯康星等三个大学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后取得的,并专门聘请了著名等离子体理论家Rosenbluth担任所长。所内十几个研究员中只有Rosenbluth、Berk、Hazeltine和Horton 4人既是研究员又是物理系教授,有资格带研究生。Horton本人曾在等离子体漂移波方面做出过较好的工作。有一天他交给我一篇打印好的文章,让我看一看有没有问题。文章的标题是“转动等离子体中的漂移波”,署名是Horton和一位从德国来的访问学者。读了这篇文章后,我觉得他们的基本方程推导有大错,没有在转动坐标系里写方程,方程中的离心力项是人为加入的。我试着推导了正确的方程,得出的结果比他们的结果要复杂得多。一周后我向Horton说明情况并在黑板上写出了我的结果,他一开始不太相信,自己琢磨一阵后,把那篇文章的首页用黑笔打了个大叉,建议我用这个题目作博士资格考试的论文。
通过调研文献,我知道了这项工作的物理背景是当时在转动等离子体实验中发现的不稳定波动模式与前人的理论分析结果不符,实验工作者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解释。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的Hooper等人在TMX串列磁镜实验中发现,转动等离子体不稳定模式的主要成分是n=0, m=1的静电槽型模,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却认定:这种模式是临界稳定的,首先出现的不稳定模式应当是n=0,m=2的模(M.N.Rosenbluth and A. Simon,Phys. Fluids 8 (1965) 1300; 9(1966) 726)。我觉得如果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个矛盾,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接受了他的建议。
经过约一年的努力,我用二流体模型推出了转动等离子体运动的基本方程,并在考虑必要的近似后,得到讨论转动等离子体线性稳定性的简正模方程,居然与Rosenbluth和Simon用复杂的动理学模型推出的方程一样。开始有些丧气,以为稳定性分析的结果也会与他们一样。但仔细考察后发现,他们解简正模方程时使用了无穷远边条件,而实际的等离子体柱的边界总是有限的。将这一条件修改后,我们得出了对应于一定的等离子体转动速度区域,m=1,n=0的模的确比m=2, n=0模更不稳定的结论。这个结果消除了实验与原有理论的矛盾,Horton很高兴,打电话告诉了他做实验的朋友Hooper。记得我在做博士资格考试报告时,所长Rosenbuluth也来听,当说到我们的结果与他原来结果不同是因为边界条件不同时,他微笑着点了头,报告后与我握手并道贺。这篇工作后来发表在《Physics of Fluids》上(W. Horton and J. Liu, “Drift waves in rotating plasma” Phys. Fluids, 27 (1984) 2067),至今仍有人在引用。这是我自大学毕业以来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
1986年5月回国前与导师W Horton夫妇的合影(左起:Wendell Horton、刘寄星、Libby Horton)
就这样,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于1983年春节回国探亲近两个月。回国期间,庆承瑞老师安排我回理论所作了一次报告,所长周光召和副所长郝柏林都来参加。会后他们曾向我表示,希望我取得博士学位后回所参加科研管理工作,我答应做两年。此外我还专门向郝柏林请教我得出的描述转动等离子体运动的非线性方程有没有办法精确求解,他看后说方程高度非线性,除非能找到将方程化为线性的变换,否则很难解析处理。
1983年春节后回到奥斯汀,我专心从事博士论文的计算工作,力图找出非线性方程的准确解,但一直苦于没有进展。于是我退而求其次,推广原有线性研究,将原来线性稳定性分析中的均匀转动改为非均匀转动,计算等离子体在非均匀转动情况下的稳定性,得出的结果非常奇怪。直观上看来,如果等离子体的转动不均匀,除了由于离心力驱动的不稳定性(类似于流体力学中的Rayleigh-Taylor不稳定性)外,还会出现由于转动剪切引起的类似于流体的Kelvin-Helmholtz不稳定性。两种因素结合的结果,必然使得体系更为不稳定。但计算的结果出人意外,剪切转动时体系反而比均匀转动时更为稳定。
这篇工作留在我手里很长时间没有投稿,直到我答辩取得学位后才投出,投出后反复受到审稿人的反对,经三次换审稿人才被接收发表(J. Liu, W. Horton and J. Sedlak, “Drift mode with sheared rotation and passing particles”, Phys. Fluids 30(1987) 467)。这篇似乎“不合时宜”文章,后来被人认为是从理论上尝试理解Tokamak等离子体L-H模转换机理的第一篇文章 (Shaing K. C, Com. Plasma Phys. & control. Fus. 14 (1991) 41),实出我们意外。原来,在我们埋头从事理论计算并为所得结果困惑那段期间,聚变实验界也正在为一个奇怪的实验结果所困扰,那就是德国的ASDEX Tokamak 在实验发现,等离子体的约束在某种加热条件下会得到改善,即约束等离子体会从Low mode 转换为High mode, 即所谓的L-H模转换。后来的实验发现,H模式的出现,总是和等离子体角向剪切转动的出现相联系的。于是,大约从1988年开始,等离子体剪切转动与L-H模式转换机理的研究成为聚变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至今仍在继续。 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对L-H模转换实验一无所知,工作的目的也只是学术性的,为兴趣所驱使。而且直到现在,我仍然说不出这个结果的直观理由。
非线性解迟迟无法求得,使我十分郁闷。Horton认为,这个非线性方程组既然求解析解基本无望,而我又在线性稳定性分析中得到了新结果,建议我像他以前的学生一样,在线性结果的基础上对问题作准线性数值分析,得出若干有关输运性质的结果后,早点毕业。我口头答应,但内心有些不甘。他不断催促我早点起草论文,使得我颇为烦躁,更难有进展。
幸好1984年暑假期间,Horton到Aspen暑期学校去了,没有人催问我要新结果,我可以自由读书,翻阅各种期刊。结果在一本气象学杂志上发现了描述Rossby 波的非线性方程Charney方程的非线性项与我的方程组的非线性项具有同样的结构。此后,又从一期《苏联科学院报告》杂志上读到,通过某种变换,Charney方程可以解析求解,而这个解就是有名的孤立涡旋解,或称为modon 解(V. D. Larichev and G.M. Reznik, Dokl. Acad. Nauk. USSR 231(1976)1077)。于是我对非线性等离子体转动方程作了变换,使得它与Chaney方程具有相同形式,接着很快求得了转动等离子体的孤立涡旋解。
1984—1985学年开学后,Horton从Aspen回来,一到办公室就问我有什么进展。我因尚未将计算结果打成文章,就简单地在黑板上给他写出了我在暑假的发现,可能是急于知道我是否按他的布置作了数值计算,他听后竟然说没有什么新东西。我有些生气,问他是否以前就知道转动等离子体的孤立涡旋,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疏忽,把我的计算重看了一遍,读后叫我把这些新结果写一个摘要,准备参加1984年秋天在Boston召开的Sherwood会议和APS会议。晚上12点他又打电话来,说希望我把原来的内容写成两个摘要,一篇写方程推导,一篇写涡旋解,分别以我们两人为第一作者,他希望当涡旋解那一篇的第一作者,我都答应了。
在10月召开的Sherwood会上,我们这项工作由Horton作了大会报告,颇受欢迎。在那次会上我还听了哈佛大学教授林家翘所作的有关悬臂星云的特邀报告,林家翘和我父亲同一年考入清华大学,林是第一名,我父亲是第41名。开会回来后将这项工作整理成文,Horton建议加Meiss博士为作者,成稿过程中Meiss博士曾多次与我讨论,出过不少好主意,我当然同意。我则建议加上为文章的数值计算作了不少贡献的Sedlak博士为作者,Horton也同意了。于是这篇颇有创意的文章是以4个人的名义发表的。(W. Horton, J. Liu, J. Meiss and J. Sedlak, “Solitary vortices in rotating plasma”, Phys. Fluids 29 (1986) 1004)
完成以上3项工作后,我觉得博士论文的内容应是比较充分了,花了约4个月时间,写成了题为《Linear instability and nonlinear motion of rotating plasma》的博士论文,期间曾认真阅读了所能找到的有关等离子体转动和流体转动的文献,努力达到John Wheeler对博士提出的标准。Wheeler是大名鼎鼎的Feynman的博士导师,当时正在UT相对论中心任教,我曾参加过一次他任答辩委员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在会上他曾讲过以下一段话:“什么是博士?按照我的看法,所谓博士就是在他所选择的研究题目上懂得最多,而且在这个方面做出别人没有做出过新结果的人。”我深信此言不谬。Winnie Schield女士非常认真地帮助我润色了论文的英文。我1985年4月提交论文,5月通过论文答辩。记得答辩会上Berk教授质疑我的一个结果,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聚变研究所的Hazeltine教授就对他说:“Shut up, Herb, he is right”,引得满堂大笑(Hazeltine教授继Rosenbluth之后当了IFS的所长,以后又当了得克萨斯大学物理系主任,我平时和他交道不多,至今我都没有想明白,他为何如此保护我)。通过答辩后,我于1985年8月获得了博士学位证书。
Horton对得出涡旋解特别得意,起草了一个简报,登在UT物理系的《研究进展》(Newsletter)上,说我们“得到了一种流体非线性运动新结构,能够解释诸如得克萨斯州长期干旱时奥克拉荷马州则阴雨连绵的现象”,我问他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他说那是个比喻。他和研究所领导商量,希望我毕业后留在研究所作博士后,于是我和IFS签了两年博士后的合同。
1985—1986年刘寄星在得克萨斯大学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时的工作证
前面我们所求得的涡旋解实际上是静电涡旋,即扰动仅为电场扰动时产生的涡旋。博士后研究的头一年,我写了两篇文章,集中研究电场和磁场均产生扰动时的涡旋结构。头一篇文章解出了转动等离子体的电磁涡旋解,并求得其传播特性(J. Liu and W. Horton, “The electromagnetic solitary vortices in rotating plasma”. Phys. Fluids 29 (1986) 1828);同时,我对当时已发表的所有有关电磁涡旋的文章进行了全面核查,发现这些文章给出的电磁涡旋解无一例外地都违反了磁场散度为零的基本定律。反复思考后发现,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这些文章的作者们错误地用静电涡旋结构来表示电磁涡旋。针对这种情况,我写了第二篇文章,这是26个印刷页的一篇长文,区分了静电涡旋和电磁涡旋的不同,提出正确求解电磁涡旋的系统方法(“The intrinsic electromagnetic vortices in magnetized plasmas” J. Plasma Physics, 36 (1986) 1)),被人戏称为“做了一个令人生畏的繁复的练习”。此后几乎所有研究等离子体电磁涡漩的文章,均采用了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的方法。现在仍有人在引用。
1986年3月,我接到郝柏林同志的来信,信不长,大意是所里的业务处长陈生忠同志生病,他忙不过来,需要我回所助他“一臂之力”,保住理论物理所这块基础研究阵地。我随即向聚变所提出辞职,于5月29日离美回国。
从1980年8月到1986年5月,我一共在美国呆了5年半左右。这段时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安心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在等离子体理论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同时通过与周围其他人的交往,对美国社会有了一定了解,结识了不少朋友。感到美国科学技术之所以领先,除了稳定的经费支持之外,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和研究者对所从事事业的执着追求非常重要。在奥斯汀的5年多时间里,我曾担任过一届(3年左右)UT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为团结中国学子、帮助解决困难以及增进与美国人民的友谊方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此外,我还在美国“嫁出”去一个“女儿”。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1981年暑假,我在物理系图书馆遇到一位“文革”时期从深圳游泳到香港、后又辗转到美国的电机系女学生王诗薇,她希望我能解答她学习物理中的疑难问题,我告诉了她我的办公室号码,请她有问题随时来问。后来她经常来问问题,那时我的朋友Darrell Gritz常和我在一起,他们也就认识了。后来俩人相互熟识、恋爱并于1983年结婚。在教堂举行婚礼时,因王的父母均在国内,她就请我作为家长,把她“嫁”了出去。可惜的是,我的这位“女婿”兼好友Darrell,4年前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实现来中国拜访我这个“老丈人”的愿望。
1984年与王诗薇(右一)和Darrell Gritz(左一)的合影
未完待续
4. “冷分子制备与操控”专题讲座第三讲:化学稳定分子的激光减速、冷却及其MOT技术
8. 理性与浪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学摄影”主题讨论侧记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