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少年惶然录

这是Epoch非虚构故事大赛50强作品的第48篇。
以下为作者原文,未做任何改动。
文 | 何乐其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在我大二快要大三的时候,有一天突然脑袋一热,想在学校做一个中文剧社。
南加州大学名义上地处洛杉矶市中心,实际被一大片很普通、甚至有些破败的墨西哥裔住宅区围绕着。到了晚上黑灯瞎火,还时常有流浪汉出没。尽管坐拥最受好莱坞宠爱的电影学院,以及在全美排名还算不错的音乐、戏剧和舞蹈学院,南加大无论如何都不是以纯艺术专业见长的;恰恰相反,我校和洛杉矶本身的精气神非常类似,充满市场化、商业化的机遇而缺乏自由的艺术气息。留学生来此就更不是为了艺术理想了——去问问任何国内的留学中介就知道,中国学生来我校看中的专业往往还是商科、工科,以及传媒类。
正因如此,想做艺术家和文化传播者的我自视清高,认为自己和那些读传播做营销的姐妹会金发姑娘不一样。大学的前两年我弹剑作歌,过得郁郁寡欢,和身边只想着实习工作创业的”大神”们无话可说。
然而,大二下学期我选修了一节即兴表演。这节课简直太有意思了!从运用身体,到训练声音,到讲一个好故事,到找寻自己的感情,每个星期都是一个全新的,关于自我的挑战。课上包容的氛围和同学们迸发的无限创意让我意识到南加大的文化环境可能并不如我想象的那般”荒漠”。学校没有友好的艺术环境是一个雷打不动的事实,也许我应该主动找一找藏在其他地方郁郁寡欢的戏剧少年。
于是带着做中文剧社的愿望,我找到了张鹤。
认识张鹤之后,我的大学生活里才有了真正的朋友。
我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不过功劳应该全部归于我。在有了做剧社的冲动之后,我辗转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才找到了隔壁 UCLA 中文剧社的社长,跟她阐述了我的想法。她说正好,我有个朋友在你学校,也想做戏剧,你们认识一下呗。我看到她发来的微信名片,头像是模糊乐队MV 里一个很魔性的蛋黄。我想这人品味不错,心里高兴了一下。
张鹤比我大两届,学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和叙事学(narrative studies),两个听起来无比高知,几乎等同于「毕业即失业」的冷门专业。当时我正要升大三,而他由于挂科太多延毕一年,正在读大五并申请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我和他一样,进南加大的时候是想读电影的,未能转院却仍然对拍电影抱有一丝可怜的、侥幸的幻想;如今又被戏剧吸引,什么都想掺一脚,对于未来同样迷茫。见到另一个自己,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他,希望这样一个朋友可以成为我所有迷茫的解药。
张鹤是一个完全的矛盾体,靠谱的同时又极其不负责任。譬如他会主动开车接送我去各种地方,把车撞坏之后却一直不肯去修。无奈之下,我俩用牛皮胶布把掉下来的部件包起来一圈一圈贴回了车身上,这样维系了两个多月他才忍无可忍地把它送修了;结果不出一个月,又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把车撞坏了。他天性里这种走心不走脑的自由散漫使他成为一个很有趣的玩伴,也是我从未有过的一种朋友。因为他展现出来的这种大大咧咧,跟他玩耍没有什么界限,也不用在意束缚和压力;这种轻松的相处状态,美国朋友们称之为”chill”,是对于一个朋友很高的褒奖。张鹤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chill friend”。
我们混在一起的一年多里,经常瞻前顾后的我也似乎变得更随性了。我和他一起吃了很多很多的垃圾食品,走了很多路看了很多戏,从他手里接过了第一支烟和第一口大麻。早在最初加他微信时,我已经完全能够想象日后这段革命友谊的蓬勃发展。于是那时的我俩在做剧社的事情上一拍即合,南加大五号门剧社就此诞生了。
万圣节的时候我穿成番茄酱而他穿成芥末酱,倒下去的那个是传承中国炒面的他的室友Solax
2016 年秋天,我们的第一出戏《薇薇》问世,在学校的地下咖啡厅勉勉强强演了两场,吸引了两三百个观众。我和张鹤担任制作人,张鹤的室友Solax 做导演,我的室友Effy 包揽了舞美,再加上招募来的舞台监督、灯光、音效数人,四位演员,20 多个人的小剧组,做出来竟也像模像样。
剧社第一批核心社员基本都是熟人。张鹤的室友Solax 也是我高中的学长,学电影制作,如今回国做摄影师月入数万;我的室友Effy 是戏剧专业,做电影和戏剧的美术设计。张鹤请来演男主角的马文则是隔壁UCLA 电影导演的毕业生,由于住得离自己学校太远选择和我们厮混。
《薇薇》的反响很好,我们第二学期的招新文案在一天之内浏览量破千,这让我们信心满满地开始筹划第二出大戏。张鹤说:"我特别希望能在毕业之前导一部戏。” 于是我们按照他的想法,把汉化版的经典英语戏剧《欲望号街车》搬上了学校最大的舞台。
汉化后的《欲望号街车》总共十一场,时间跨度一年多,有大段大段的独白、微妙的心理变化,还有一场打戏、床戏和一场强奸戏——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制作上还是表演上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每周二周四夜里和周六都被排练侵占,之后大家便驱车前往韩国城吃夜宵,也不知是为了庆祝还是反抗。随着演出越来越近,导演组变得愈发手忙脚乱;排练的战线越拉越长,尔后吃夜宵放松也就越来越频繁。很快,我的社交生活就真真实实地只剩下五号门剧社了。我们工作日一起排练一起吃,周末喝酒聊天打桌游,假期爬山滑雪泡温泉,粘腻得像群居的野兽。
不排练的周末我们就去KTV 唱歌。洛杉矶华人区,我们最常去的KTV 叫Energy,一般分摊下来每人二三十美元。但如果想喝酒就得去贵得离谱的K-republic,能唱出一人一百刀的天价。
洛杉矶的无聊主要体现于夜生活的匮乏——法律规定凌晨两点之后不能卖酒,于是大部分出售酒精的娱乐场所都是两点关门;Energy 不卖酒也只开到三点,也不知道这么早关门图啥。入夜之后,祖国同胞消费的意愿往往指数增长。不料在最容易冲动消费的时间段花钱的渠道竟然都关门大吉了,特别lame,不酷。每一次我们都能从十一点唱到三点,整家店都给唱空了我们才刚嗨起来。最后几首歌我往往会顺次点万能青年旅社和草东没有派对的歌。服务员五次三番地推门进来,客客气气地求道:「那个……我们要关门了啦。」尔后在我们「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的大吼大叫中节节败退。
张鹤唱歌走调,对此很为介意,每次都跟我们出来,每次总不唱。一个人默默在旁边坐三四个小时,最后和我们分摊一样多的钱。只有当《大石碎胸口》,《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或者《山海》、《大风吹》前奏响起的时候,他会跳上桌子甩起头发,争夺我的话筒,勉力发出一些没人听得见的嘶吼。
一个次日早晨要联排的周五深夜,马文参加唱歌比赛拿了亚军,我们为了庆祝就去Energy 唱到了三点。从KTV 出来,意犹未尽的大伙儿像是想当黑帮的高中生一样,一字排开坐在楼道口。想来想去不知道该干嘛,于是转场到学校一幢宿舍楼的大厅里,坐在台球桌边继续沉默寡言。
当时的气氛非常古怪,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话中既有暗流涌动的微妙情愫,也有积压已久的生活残骸。大家本都不顺心,假借这次「嗨」的余温沮丧一把。张鹤前几天悄悄告诉我他电影学院的申请已经全部被拒了。延毕之后又无研可读,他依旧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谈论着要做导演要做演员。在台球桌边他递过来个眼神,用嘴型问:「我要告诉他们咯?」之前一直拜托我不要告诉别人,此时又想要宣布这件事,我从他不确定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慌乱。我觉得他更应该担心会不会把大戏也搞砸了,尤其因为大约六小时后就要第一次联排,我们却还在这里谈论着无药可救的惶然。淹没在巨大的悲伤泡泡里,我硬生生把这些话吞了下去。
所有人都知道第二天有非常重要的大彩排,然而所有人都佯装疯狂且真诚,以至于不想扫兴散场。「离开」像是一个没有人敢触碰的魔咒,会把我们之间强烈的相互需要击破。于是大家在困倦和沉默中僵持着,在被黑布罩上的台球桌上或坐或躺,东倒西歪地赖在彼此身边。
张鹤在毕业数月之后依然没有找到稳定工作,租住的房子即将到期,家人不断催他回家。他变得越来越阴沉,整日把自己投入进游戏和Youtube 的怀抱。离开这里对他来说,显然是一个他在不断逃避,但也很难逃避更久的事情。我们之间的友谊和一起奋斗的艺术理想,如他表面上的随性自由一样,闪耀和消沉在未来的不确定性里。
五号门剧社的戏剧少年们依旧苟延残喘在制造梦想的大洛杉矶。我们遮住双眼蜷缩在彼此的臂弯里,用短暂的温暖来拒绝未知的茫然和恐惧。
50强作品微信评选规则
8月18日起,50强作品在“每日人物”微信公众号上推送展示,统一按照作品提交顺序发布,每天发布2部。72小时后,计算单篇文章点赞数总和。微信评选期间,评审组对50强作品进行交叉打分,得出单篇文章分数。
单篇作品总分=微信点赞成绩(15%)+评审组作品打分(85%)
50强微信评选全部结束后,总分前10名进入决赛,并来京进行现场比赛,角逐一二三等奖。10强名单将于评审结束后在刺猬公社、每日人物、AI财经社微信公布。第11-50名分别对应优胜、优秀、入围奖(具体请查看大赛奖项)。
注:主办方将实时监测点赞数据,坚决杜绝刷票现象。“清博大数据”独家提供全程数据监控支持,一旦发现有刷数据行为,取消比赛资格。
▼
主办:刺猬公社 每日人物 AI财经社
特别支持:蚂蚁金服商学院

文章为原作者授权发布,侵权必究。
后台回复“进群”加入每人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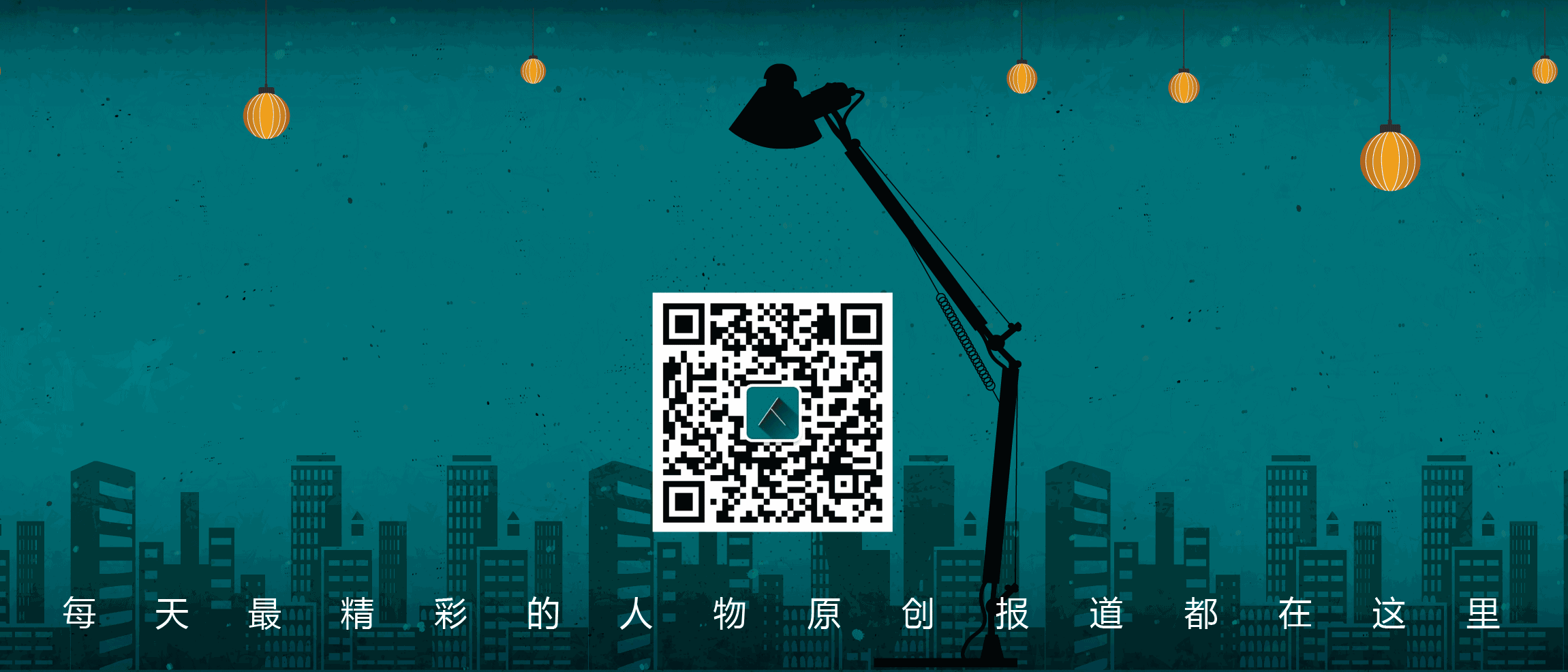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50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