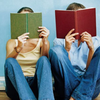考试机器是怎么炼成的
薛涌:考试机器是怎么炼成的
本文节选自作者为《科场现形记续编》(郑也夫/编)所写的序言,作者为旅美学者薛涌。中信出版社供稿。
“开学第一天,交通早高峰提前半小时到来,交通压力明显上升,达到‘轻度拥堵’ 程度。学校周边交通压力尤其突出。”
这是最近一篇“小升初”报道中的开篇文字。地点是北京。何以如此?报道举出一个例子:
“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顾婷一家的境遇似乎能给出答案——早上6 点钟起床,带着孩子毛毛穿越半个北京城去另外一个学区上学。”
在北京,你不知道有多少毛毛这样的孩子。这意味着家长陪着孩子每天两三个小时耽误在被雾霾笼罩的路上,还有8 万的“择校费”。而这仅仅是“幼升小”。
“有家长早就安排孩子上了幼升小的面试培训班,准备并背下了中、英双语的自我介绍;有的家长记录下每个学校重视的特长,英语、体育、民乐……”
下一步当然更为惨烈,即所谓“小升初”。为了达到目的,出现了“占坑班”“共建生”“推优”“派位”等名目。因为最后效果不同,“占坑班”又被家长们分成“金坑”“银坑”“土坑”“粪坑”等。
为“小升初”而“占坑”,最近日益引起媒体的注意。但《科场现形记》中北大2009 级社会学系本科生刘雨甲同学《小升初中的“占坑班”调查》,大概是最早对这一病态的择校战的社会学“深描”。为了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所涉及的学校、机构、学生、家长的名字都采取化名。但调查本身,则遵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建立在大量访谈基础上,为我们勾勒出了相当复杂的教育体系。
调查所描写的“小升初”之战,围绕着国有民办的A 中学展开。要进这个学校,小学生们首先进入一所叫“果实培训学校”的课外辅导班去“占坑”。因为A 中学每年提前从这所培训学校秘密录取许多学生。然而,这所果实培训学校也有入学考试,录取率仅40%左右,于是又催生了另一所培训学校“紫优”。“紫优”所培训的内容,是应付A中学的入学考试,同时辅助那些在“果实”读书的孩子在班上能够出人头地。也就是说,一个好中学,有个专门为之输送生源的“正室”,还有个“二奶”。当然,“正室”和“二奶”之间难以和谐,“正室”频频声称自己是唯一可向A中学推荐学生的机构,其他几个机构宣称的推荐都不属实。但是,这挡不住“二奶”“小三”们的势头。大部分孩子,都会上两个以上的课外培训班。
“正室”的课程,是一个整上午。“二奶”的课程,则是一周2次,每次3个小时。这样算来,一周大概就快10个小时了吧。不用说,还有孩子上第三个培训班,也有跟着家教上课的。当然,还要算上交通的时间。许多孩子,因为忙于在学校和各种培训班之间穿梭,连吃晚饭的时间都没有。
家长在网上吐槽: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怎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坑班世界/掏走钱财,花钱没谢/你怎能把握这焦灼不安的季节/烦恼最是无情夜/测评考试难说那就是真点/成绩也未必就代表一切/你知哪句是真哪一句是假/哪一句算择校终结……”
结果如何?孩子过度培训,重复学习,有些上培训班多的孩子,开始在正常的学校课堂上捣乱。占坑班中竞争激烈,同学关系紧张。中学的入学考试和小学教学脱节,靠小学学的东西无法应付小升初的竞争,必须额外上培训班,义务教育名存实亡。
当然,最为糟糕的是,孩子们如此废寝忘食地努力,全为了考试,而且全为了A中学这一特定的入学考试。孩子们的成长,不是放眼不断在生活中展开的大世界,而是钻进越来越小的牢笼。
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一生恐怕都会有心理障碍。比如,我指导过一个准备留学的学生,英语程度很好,人也勤奋好学,进步很大。但后来突然中断,称要准备雅思。可惜雅思又考得不理想,意气消沉,有些厌学。我和家长讲:以他的程度,在美国读个像样的大学没有问题。家长赶紧说“不可”,因为孩子准备的是雅思,去美国则要考托福、SAT。我大惑不解:不都是英语吗?怎么考雅思的就不能考托福?家长说孩子早早都定向选择了自己的“目标学校”,乃至中学里的学生和家长中按留学去向形成了所谓“美国党”“英国党”“加拿大党”“澳大利亚党”…… 你入了哪个“党”,就准备哪个“党”的考试。“英国党”只熟悉雅思的题型,搞不明白托福是怎么回事。大家似乎已经在告诉我:学的是特定的英语考试,不是英语!
如此炼就的考试机器,还能够应付真实的生活吗?
美国的小升初
《科场现形记》读来最让人唏嘘之处,是中国的孩子还在懵懵懂懂的年纪就要上科场:幼升小,小升初。
科场对儿童的心理发育有巨大伤害。欧洲几个国家一度也受应试化的影响,幼儿园里开始读书识字,也有考试。结果,后来的追踪调查发现:这些孩子虽然一时间学业领先,但上了小学几年优势顿消,小学毕业时则比幼儿园时不学习的孩子落后。如今德、法等国,已经明令禁止在幼儿园阶段讲授文化课,更不用说考试了。
那么,在西方发达社会,孩子没有择校的问题吗?大体而言,在西欧,至少这样的问题不严重。那里教育资源分配比较平均,一般学校都能保证质量。美国情况比较复杂,我也和孩子亲身经历过。不妨略述一二,作为和中国孩子的对照。
比起西欧来,美国义务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源分配不均:以学区制为主导,学区的教育经费主要靠本地房地产税。于是,富裕的高房价区学校资金充足,贫困学区则只能将就。这样,贫富分化导致下一代的教育分化,教育分化进一步加深贫富分化。现在不仅仅是贫富分化,而且是贫富隔离。穷人富人根本不住在一个地方。大家老死不相往来。孩子们也自然在两个世界中生活。
但即使如此,择校的压力全在父母身上,而不在孩子身上。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 要选择一个好的学区,这意味着得买得起比较贵的房子。实在买不起,就租一套。只要住在那里,拿个写着自己名字和地址的信封,到学校的接待前台5 分钟就入学了,不需要任何手续。另外,美国绝大部分地区,房价不像中国大都市这么疯狂。
以我女儿就读的这个学区为例,高中曾几次进过全美百强,最低也在第150 名左右,算是顶尖了。为了孩子上学买“学区房”,三口人挤一点,买个100 平方米的连体式新房,也就16 万美元,还是镇中心最方便的地段,走几步就到学校了。三口之家只要有一个人工作,有六七万的平民收入,支付起来还是绰绰有余。一般而言,即使是中低收入,也会买个很不错的房子。
我们搬到这里,是因为要保证女儿上好的中学和高中。搬家是在女儿小学五年级时,希望她有一年的时间结交朋友,然后一起升中学。所以,她刚转到这里的小学后, 马上就赶上了小升初。小升初没有任何考试。但孩子们来年要从现在就读的小学转到马路对面临着湖区并和高中连在一起的中学,也是个不小的人生转折了。
这个镇的小学,为了小升初有个传统的仪式,就是所有小学毕业班的学生到外州的一个野营地参与为期一周的“自然课堂”学习。问问那些本镇土生土长的大人,小学什么最难忘?几乎所有人都会告诉你是“自然课堂”。对许多孩子来说,这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参与集体生活,夜晚住在森林里的小木屋,进行各种野外生存训练。
女儿回来时还教给我们怎么吃蚯蚓:把蚯蚓剁成几段,因为蚯蚓有几颗心,不会死,只要留一段放生就行。从小娇生惯养的她,居然真试着自己烤蚯蚓吃。夜晚孩子们围在篝火边海阔天空,最后的一个节目则是所谓“唱倒”,即大家一起唱歌,唱着唱着,就又累又困地睡倒。毕竟在森林里跋涉了一天,上了各种生物课,辛苦得很。
总之,“自然课堂”的主题就是让孩子超越现有的文明,回到大自然原始状态,让自己的想象张开翅膀,带着种种儿童的梦幻升入中学。
我曾一再强调,说美国的学校是儿童乐园、不用读书、整天玩儿等等是以讹传讹。美国的好学校中的好学生,并不比中国的孩子轻松。女儿现在14岁,刚上高一,上学时一天就睡6个小时,累得要死要活。这些且留待后面再说。不过,这使青春期的孩子,开始有了成人的责任和压力。小学生则还属于儿童,仍要保证他们有足够的空间沉浸在孩子的世界中。童年和青春期是非常不同的成长阶段,心理构造十分不同。把孩子那么早赶到科场,无疑是对儿童的摧残,闹不好日后会引发各种成长障碍。
重点班的得失
中国的孩子“小升初”之后,马上还有“初升高”,然后就是高考。科场一个接一个。和“初升高”及高考紧密相连的,就是高中的“重点班”。
在《科场现形记》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1级研究生蒋越同学的《重点班:进入与逃离》,通过对江苏A市B高中(即全市第二号高中)的调查而聚焦于这个问题:教育资源的分配,不仅在地区之间不公平,在同一地区的学校之间不公平,甚至在同一学校中也不公平。
“重点班”是中国的学生和家长最熟悉不过的现象。这所高中设“重点班”,也是基于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情况下争取更多资源的战略考虑。该高中在全市排名老二,与老大竞争力不从心。于是,就集中资源,用最优秀的师资办“重点班”,至少保证“重点班”的教育质量和全市的老大平起平坐。这样,一来保证能从初中吸引一批优秀学生,二来也能保证这些学生考进好大学。当然,升学的业绩提高学校的声誉,最终可以带来更多的资源。
这个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恢复高考时就普遍使用,而且非常有效。当时,笔者就读的北京145中学,是一所“文革”期间由小学升格的中学,质量不佳。但是,所在地区有些不错的生源,乃至高年级中还有获得北京数学竞赛第一的学生。
高考刚刚恢复,虽然还没有所谓“重点学校”的制度,但事实上的“重点”已经形成。附近的171中学,马上以突出的升学率把周边地区的好学生吸引过去。
面对这种情况,145中的老师对我们几个“好学生”开诚布公:“我们确实不如171,但是,我们把最好的师资都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你们在这里比去171更有优势。”
就我所在的文科班而言,班主任特别强调:“你们三个顶尖学生,肯定上大学。其他人,怎么努力也没用。全校最好的四个文科老师就围着你们三个转,外加一位优秀的数学老师。五对三呀。到了171,你们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吗?”我听了后毫不犹豫地留下。等1979年高考时,我果然考到文科类北京前15名,成绩据说比171最好的学生还高20分左右。
有了这样的亲身经历,读蒋越同学的调查报告就备感亲切。江苏A市这所B高中,设置了两个“重点班”。当时江苏高考沿用3+2制,语文、数学、英语必考,另外在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六门中任选两科。该高中根据本校师资情况和高校录取的口味,鼓励学生在选择性科目中选择物理、化学组合,并以此作为进“重点班”的先决条件。虽然形式复杂不少,但基本做法和我们那个时代一脉相承:最好的师资用来教育最好的学生,“重点班”的学生为天之骄子,是全校的楷模。老师对非重点班的学生指指点点:瞧瞧人家,又聪明,又肯吃苦奋斗。再瞧瞧你们,比人家笨,还不知道努力!
不过,这篇调查虽然非常细致,其核心结论则似乎有些武断:“那么功利、武断地对学生进行分等,将校内的教育资源向所谓的‘高能’学生大幅倾斜的做法”,有失教育公平。
在我看来,问题似乎还远非这么简单。
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一直都有“重点班”,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这些国家的公立学校对学生来者不拒,无权甄选,学生素质自然参差不齐;要想因材施教,只有设置“重点班”。
其实,郑也夫的《吾国教育病理》中,专门有一章讨论德国学校对10 岁孩子“分流”,尖子生走入大学轨,就是大学预科(gymnasium),普通生进入技工轨。这其实是相当严格的“重点班”制度。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大学预科的制度,并非仅仅限于德国,许多欧洲国家都实行。比如荷兰,大学预科是其大学学前教育(VWO)的一种。另外,在德国,大学预科也许没有“重点班”,因为大学预科的选拔本身就很严格了。但是,在荷兰,学校里往往把不同能力的学生分到许多不同的“轨”上,其实这就是相当系统的“重点班”了。
这里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考察中国的教育,往往看到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 似乎都该矫正。其实这不太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有个优先的选择,并把每个孤立的问题放在宏观的制度框架中来考虑。“占坑班”和“重点班”就是很好的例证。表面上看,“占坑班”和“重点班”都有许多问题,似乎都应该清除。其实,要想清除“占坑班”,往往需要大力发展“重点班”。只能抑此扬彼,不能两者都一味反对。
在我看来,要达到教育公平的目标,首先要解决地区与地区、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公。重点学校要取消,所有学生按照居住地区就近读书,临时住户有地址也能入学。
目前教育部的改革思路,仍限于初中就近入学,高中按分录取。在我看来,这样远远不够,应该高中也就近入学。这样,就彻底省去了择校的竞争。但是,一旦没有择校问题,每个丧失了甄选学生权力的学校,就必须来者不拒,学生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恐怕一下子会变得比现在要突出得多。面对这样的情况,恐怕不仅要有“重点班”,还要有“次重点班”等更精微的分层。
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如果又要禁止择校,又要禁止“重点班”,其实就等于同时颁布两个互相矛盾的政策,让学校无所措手足,家长和学生也不会满意,最后逼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老游戏。在这方面,还需要更为宏观的政策讨论。
从“小升初”前的“占坑班”到高中时的“重点班”,无不体现了中国教育的恶性竞争。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郑也夫的《吾国教育病理》有不少讨论,可以和他指导学生们进行的社会调查进行互证。
在郑也夫看来,中国教育的恶性竞争之所以成为几十年的痼疾,最大的原因就是教育目标的单一。几乎所有中小学的学生都奔着大学这一目标。那些中职生,72%是因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不得已而求其次。技工教育的沦落,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竞争力。
-END-
特别推荐★★★★★
《科场现形记续编》郑也夫 编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入思想潮小书店看看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