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压正》:纷乱世上觅天然
关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101篇原创首发文章
姜文新作《邪不压正》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清丽,而非他以往作品中肆意昂扬的跌宕与热烈。
表面上看,在荷尔蒙与力比多之间起中和作用的是张北海笔下的北平风味——月牙、阳光、树影、砖墙、前门楼子、胡同巷弄,这晦暗时代中的诸多景象,于今人而言已是遗失了大半个世纪的亮色。或许只有如那位写《侠隐》的旅美作家一般的亲历者,才能破解这抹亮色的失真与梦幻:“有时候,我坐在纽约的高线花园里,闭上眼睛,就觉得自己像是坐在西直门的城墙上。”
根本上讲,姜文从无意于在《邪不压正》里重复张北海在《侠隐》所讲的故事,与其说姜文对张北海的文本进行了改编,不如说前者对它进行了再创作。既然是再创作,既然没有过分受影响,为何创作者仍会压抑自己的原有笔法,使得《邪不压正》不复《让子弹飞》式的“大片叙事”?可如果你真的怀疑“姜文变了”,倒不妨先问问“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的沛公为何在入关中之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答案无非“此其志不在小”。
最擅长讲故事的姜文,此番的志向却是在《邪不压正》里“不讲一故事”,乍听上去有些离经叛道。依我对姜文的浅见,看似狂狷的他不仅最能下死工夫,更是不会无来由地去离经叛道,不管是天道、世道还是他自己的道。他之所以不讲“一个”,或许是为了讲好“无数”。
电影中李天然这个角色的人物设计,与其说来自张北海的那部小说,毋宁说跟彭于晏在《明月几时有》里扮演的岭南抗日英雄刘黑仔更像,一样的生逢乱世、单枪匹马、身怀绝技,要知道许鞍华那部作品的编剧何冀平此番也参与了《邪不压正》的剧本创作。
与刘黑仔的不同之处在于,李天然身上具备一种自觉性(姜文语),关于一个人的成长和变化、挣扎与怀疑,而且最重要的是主人公在实质意义上的关键节点完成了扭转,这种自觉性是姜文电影中以往角色所不具备的——马小军从房顶上落了地,他就失去了米兰;张麻子扳倒了黄四郎,其部属却离他而去。一言蔽之,和李天然相比,他们并不知道各自的问题出在哪儿?因为那些问题很可能不是他们造成的,而是他们所处的世界造成的。
在《邪不压正》里,主人公解决问题的路径便是“复仇”。15年前,师兄朱潜龙勾结日本人残忍杀害师父全家,李天然侥幸生还,被美国医生所救。15年后,李天然由美国学成归来,北洋进阶民国,仇人位高权重,时局纷繁复杂,世道几经更变。在外界造成的巨大悲剧面前,李天然不假思索地跳上房顶,在个人经历与历史叙事的夹缝中穿梭,一面是小楫轻舟,一面是波澜万丈。
关于电影的主旨,有人看到了秘不可宣的历史,有人看到了少年与御姐的爱情,有人看到了莎士比亚戏剧式的复仇。试问,一部能够提供如此之多讨论切入点的电影,又怎会沦为“不知所云”的晦涩之作?我着实不理解《邪不压正》有什么好骂的,更不理解那些连看姜文电影都要思量一下该不该买票入场的人,为何为烂片买单时动作那么娴熟、内心那么坦然。至于那些看过电影仍然颇有微词的观众,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些缓解失望情绪的灵丹妙药:
想看对于老北平呓语般的追忆,那就多读几遍《侠隐》;想看原汁原味的民国武林,那就去看徐皓峰;想看姜文把他的每部作品都拍成你想看的样子,不如先扪心自问一下,你是给电影创作者提供创意了,还是哗哗往里砸钱了?
至于那些影评人,你可能见惯了他们的伶牙俐齿与头头是道,直到有一天他们谈起一个你精通的领域,或者你熟悉的事件,你才明白什么叫哗众取宠,什么叫强行刻奇,什么叫不懂装懂,什么叫故作腔调。他们不是在“评论”,他们是在“毁坏”。
姜文对于影评人的诟病由来已久,此番他也特地在《邪不压正》里量身定做了嘲讽影评人的段落。至于编剧史航饰演的那个满嘴“之乎者也”的影评人,在电影中外号为何叫“公公”,看看姜文早年的那句话就明白了——“很多影评人就像太监,净瞧皇上办事了,自己只会瞎琢磨。”
《邪不压正》里的北平是荒诞不经的。
美国医生亨德利在北平的街道上飞扬跋扈地开车,不避让行人,还美其名曰“入乡随俗”,这很荒诞;
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将文坛泰斗梁启超健康的右肾切除,留下患病的左肾,导致梁启超的壮年早逝,这很荒诞;
蓝青峰说蒋介石在日记里写的实际上是心里话,朱潜龙说老蒋有病就有病在这,政客实在一回,反倒被说是有病,这也很荒诞;
当荒诞不经成为一种常态,正常便会成为一种突兀,这是电影中那个民国的真相,也是所有凡尘俗世的真相。《邪不压正》的叙事既不乱、也不散,创作者只是在铺陈世界本身的粗糙与混沌,那些鸡零狗碎又自得其说的部分,属于历史,也属于未来。
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拍得太乱,恰恰是因为电影的细节拍得太真实,拍得太接近生活本身而非戏剧理论中关于生活的想象与建构。姜文当然可以把生活拍得更有序,但前提必须是生活真的是有序的,是让那些讲理的人、认真的人、自然的人活得更顺更妥帖更称心如意的,如果“生活”做不到上述这些,那么姜文就宁可还原这种变质生活的“既让人没法生”和“又让人没法活”。
至于什么叫做“真乱”,便是没看过经典的人说经典晦涩难懂;是不认得几个字的人斥责辞藻佶屈聱牙;是大众毫无道理地偏听偏信、人云亦云;是滥竽充数者“料他人应如是”。如果一整个世道都流行这些,这样的世道便是乱世。
结合电影去看,李天然孤军深入的世道之所以是乱世,乃是因为他的本性过于赤诚与纯良,换个人去适应,比如奸佞朱潜龙或者老油条蓝青峰,“如鱼得水”和“手拿把攥”这类关键词就会被扶正。李天然要做的事情,表面上看是在进行一场难度系数极大的复仇,实际上是在努力理解一个礼崩乐坏的世道的生存指南,并在其中找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密码。李天然像走兽一样在屋脊上闪展腾挪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隐喻,关于行动,关于行之有效,关于行知合一。
电影在进行上述略显深邃的题旨的同时,剧情里显露出的一切均是经过考证与编排的,看似写意潦草,实际上非常讲究、细致。抛开剧情和寓意不谈,即便是冲着这份讲究与细致,观众也应当致以相当程度的敬意,而不是急着落井下石。
《邪不压正》的细节的确讲究,比如电影中露面不超过半分钟的张自忠,他在被蓝青峰接上车时只有一句台词,演员的口音用了山东口音。张自忠将军是山东临清人,口音的细节便是考证过的,姜文就是能细到这个程度。
再比如李天然前去复仇时,“七七事变”到平津失守前北平城的时局,电影里也有一明一暗两处细节与历史呼应。明的那处是日本特务在街头枪杀人力车夫,听见枪声维持秩序的却不是中国军队,而是为虎作伥的警察;暗的那处是蓝青峰送李天然比武途中,车上照会他,29军已经撤走,日本兵还没有进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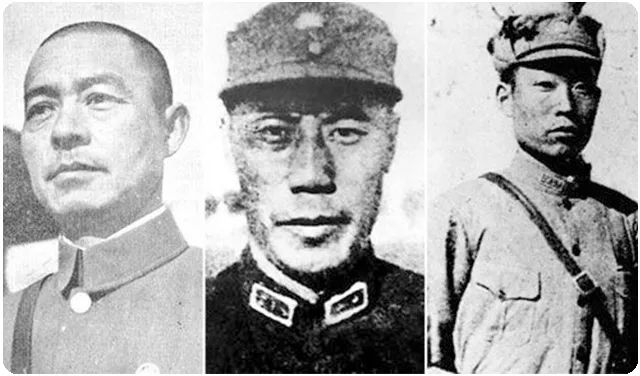
当时的情况正是,南苑要地因汉奸出卖而遭日军突破,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华北防线被拦腰截断、大势已去。29军军长宋哲元为保留实力,委任38师师长张自忠为代理北平市长,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谈判,企图拖住日方攻势。29军残部在南苑沦陷的第二天便撤离了平津防线,仅留下4个团来维持治安。北平城的中国军力瞬时成为真空状态,日本军人、特务、浪人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这也正是电影末尾反派开始大举反扑并且气焰嚣张的原因。
如果你熟悉上面这些“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的历史细节,你便知道在那些影评人“分析来分析去也分析不到点子上”的历史纵深处,姜文已经走了多远!这样的人做事不是为不懂的人做的,而是为懂的人做的。懂的人可能很少,而且不懂的人可能永远也变不成懂的人,他们不懂的事情或许永远也不会懂。但那又如何?
姜文在《圆桌派》里讲过,自己之所以找了一批一米五多的中学生去扮演日本兵,是因为结合老照片复原三八大盖与日本钢盔之后发现,那时候的侵华日军普遍就该是那个身高。窦文涛于是问姜文,日本鬼子比枪高还是比枪低这件事,对今天的年轻观众来说,意义究竟在哪里?
面对这个刁钻的问题,姜文的回答堪称经典:“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我觉得他今天不懂,他有一天会懂的,等他懂的那一天回来想——老姜真对得起我……我对得起他小时候无知的时候,但没关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我对得起那时候就够了。”
关于电影的名字,《邪不压正》和《侠隐》的腔调完全不同。之所以叫《侠隐》,是因为世道太乱,令包括侠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所适从,旧的规矩已经破碎,新的秩序仍在颠倒,人们苟且偷生,不得不窝着。但侠从来是不甘寂寞的,地上若是没有立锥之地,那就在房顶上出现,砖瓦之上似有一个清平世界,与污浊现世平行共存。侠隐中的“侠”,是一种步履坚定的叛逆;侠隐中的“隐”,则是一份迫于无奈的浪漫。
清末程派八卦掌宗师程廷华便是这样的隐侠,崇文门外经营一家眼镜店,从不多生事端。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入京师,生灵涂炭。程廷华气不过,便于夜间提一把单刀走壁飞檐,遇见落单洋鬼子便跳下格杀之。动静一多,被洋人盯上,最终殁于侵略者的乱枪之下。
但叫《邪不压正》的故事就不太一样了,主人公不再隐于市朝,他试着从所有表面文章中跳将出来,彻底认清周遭的世界。
电影开场弑师的桥段有个特写,朱潜龙朝师父开枪,后者眉心中弹,本能性地发功运力,想要手刃逆徒。但师父离朱潜龙还有数步之距,他的掌力拍不到逆徒身上,接着朱潜龙开了第二枪。想想王家卫的《一代宗师》,马三同样偷袭了师父,但他用的仍是师父所教的拳术,近身得手后还被师父用最后的力气打出门外。
所以说,《邪不压正》的世道比《一代宗师》的世道更乱、更险恶,因为坏人直接上枪,不讲理的人不讲的可不单是“理”,连“情”都不讲。如果李天然坚持他的“月棍年刀一辈子枪”,那他最后一定数不清身上到底多少个枪眼。他想要复仇,就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把刀枪换成手枪,二是不信拿手枪的人说的话。
第一件事容易,李天然在美国受训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第二件事困难,难住了他回到北平之后的大部分时间。直到他遇到关巧红,后者告诉他,复仇不用别人信,“一个人,一把枪,足矣”。电影中关巧红的原型是侠女施剑翘,她卧薪尝胆整整十年,直到亲手击毙杀害父亲的军阀孙传芳。关巧红这个角色对于李天然的意义,就在于她以己为例破解了后者的心症:不管在何种境遇,一个人都应当明辨是非、内心强大、步履坚定,别的不用想,想了也是白想。
为什么想了白想?因为坏人重塑了规则、篡改了真相,就像电影里的朱潜龙,摇身一变成为大英雄,成为不可撼动的形象,受世人顶礼膜拜。你跟他讲规则,他跟你讲道德;你跟他讲道德,他跟你讲法律。总之一直会绕来绕去,让你找不到发力点。跟颠倒黑白的人讲理,永远讲不清。这时候还在乎社会评价,请问你怎么在乎?
《邪不压正》令我想起一个是非题:一个快饿死的人倒在屋子前,被屋主人救了。接着,屋主人被害,凶手成为了新的屋主人,屋子也变成了他的屋子。再后来,那个被救的人回来了,他想向屋主人报恩,试问他应当向屋子的主人报恩还是实际救了他的人报恩?如果这个人能明辨是非,向实际救了他的人报恩,他此刻就应当向屋子现有的主人报仇,这便是电影;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人真的就“认贼作父”了,将屋子现有的主人视为恩人,这便是历史。
李天然跟朱潜龙对质的时候,后者百般无赖,拒绝承认错误。李天然用了一计,他问朱潜龙,如果师父答应日本人种鸦片,你还害师父吗?后者果然中计,他回应道,那我还杀他干什么?就在朱潜龙说出这句话后,李天然扣动了扳机,他就是要等坏人的谎言被自行拆穿后再杀之,这个“讲理”的过程实际上是做给观众看的。李天然当然知道是谁杀了师父,借着上帝视角去看了整场电影的观众也知道,可如果《邪不压正》不是电影,所有人变成了普通视角,周遭充满着被迷惑被欺骗的可能性,又有多少人能够笃定谁是正,谁是邪?
历史的糊涂账太多,所以唐德刚在诗里写道:“劝君莫论中原事,且乘歌声舞一回”。再回到电影里,李天然完成了复仇,他终于理清了以往的纷乱,但所处的时代环境却比从前更乱,更不可控,日本人昂首阔步地进城,红颜知己亦不知所踪,新的困境接踵而来。李天然已经学会了一手拿刀(旧秩序),一手拿枪(新规则),但在从未停止却又不合逻辑的“变化”面前,他永远显得滞后,永远手足无措。
姜文是悲观的,也是客观的,他安排主人公达成戏剧意义上的使命后,没有授予其“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权利,而是又带着他看到了生活更深邃的真相。
作者:92年生,金牛座,爱文艺、喜昏睡。秦朔朋友圈专栏作者。
「 图片 | 视觉中国 」
秦朔朋友圈微信公众号:qspyq2015
商务合作|请联系微信号:qspyqswhz
投稿、内容合作、招聘简历:friends@chinamoment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