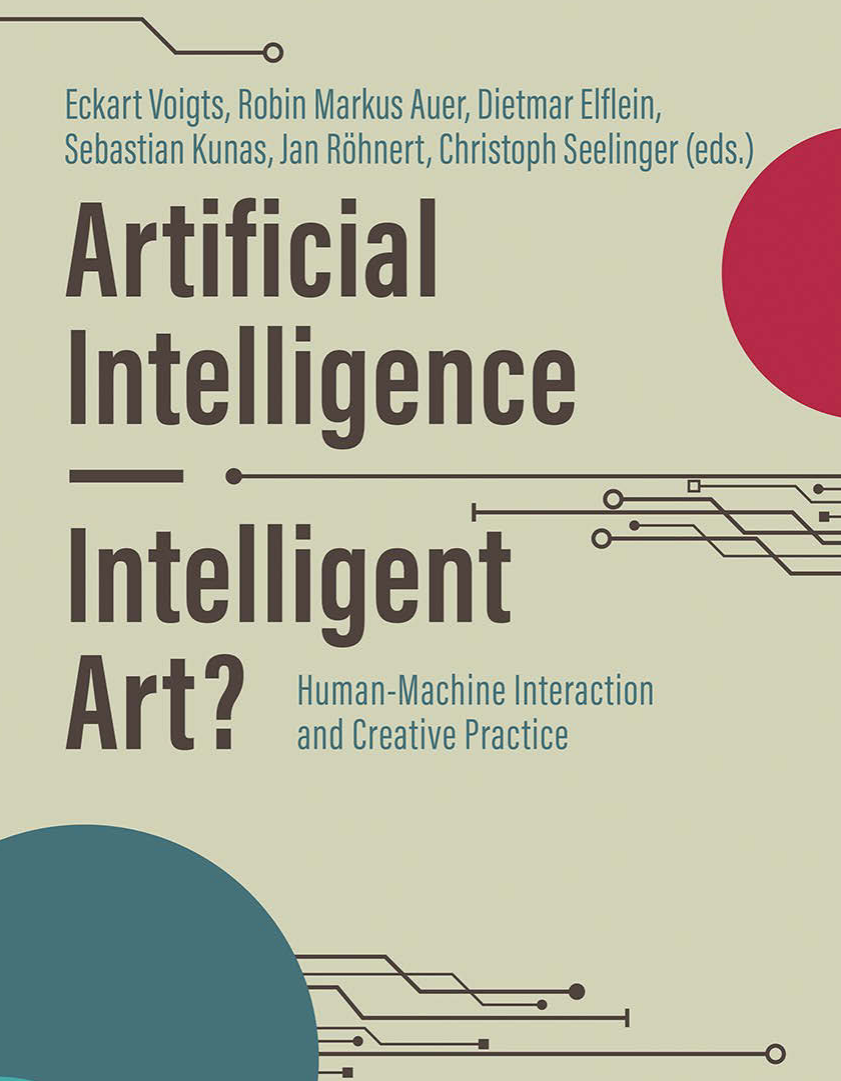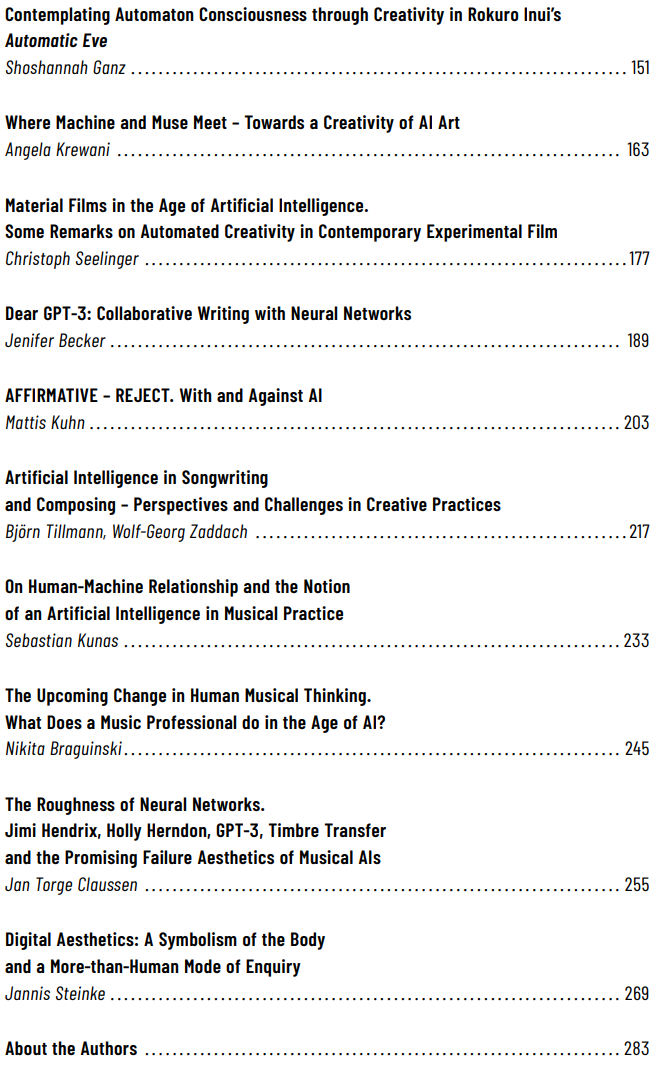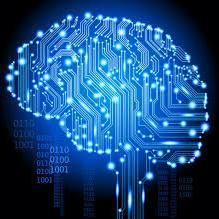人机:从古希腊到 ChatGPT
本卷对电子媒体数字编码背景下出现的算法 “创造力 ”的形式和后果进行了批判和评估,对既有实践、道德规范以及创造力概念进行了挪用、补充、叠加和改造。相互连接的数字世界拥有大量可用数据,在此被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其复制、转换和改编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
随着算法数据处理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它也开始进入艺术、文学和音乐领域。在此过程中,它转变了创造力的概念,并唤起了人们对艺术实践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探讨这一发展在美学、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影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本卷旨在为此做出贡献。虽然许多探索和研究领域都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挑战做出了回应,但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在艺术实践中的作用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和科学对社会(Manyika 2022)、教育(Holmes 等 2019)、经济(Brynjolfsson 2014、Agrawal 2018)、政治和媒体(O'Neil 2016、Sudmann 2019)以及军事(Scharre 2019)的影响的批判性辩论,自 20 世纪 50 年代该术语最早出现并在制度上实施以来,就一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虽然人工智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医学和其他领域的有用应用,或人工智能发展的政治、伦理、法律、哲学、社会、教育、军事和经济层面,但直到最近,文化和美学方面的关注才成为更清晰的焦点(米勒 2019 年、马诺维奇 2018 年、2019 年、齐林斯卡 2020 年、泽林格 2021 年、哈格贝克/赫德布洛姆 2021 年、雷克-米兰达 2021 年、舍恩塔勒 2022 年、莫尔曼/鲁斯 2023 年)。本卷也遵循类似的轨迹,力求重新连接和调整人工智能的讨论,以便考虑到文学、电影、艺术和音乐中艺术实践的文化维度。
通常,人们似乎很难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更广泛的数字计算领域区分开来。事实上,人工智能的术语与 “自动化 ”的论述密切相关。“自动化 ”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术语,不仅包括前数字世界,还包括旨在实现流程自动化(即自我管理)的首批先进技术。因此,自动机是自动运行机器的一种特例。人们通常认为,人工智能世界中的自动化是指任何超越了单纯的软件编程和算法(即 “如果-那么 ”的规则管理世界)的应用,而是使用机器学习的过程、可修改的算法,因此,数据处理超越了单纯的算法指令(但不可避免地包括代码规则)。因此,人工智能系统是任何能够感知环境并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成功实现目标的设备。
关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力量和发展,人们展开了各种辩论、争论和预测。以雷蒙德-库兹韦尔(Raymond Kurzweil,2005 年)为首的人工智能爱好者预测,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在 2045 年左右带来他所说的 “奇点”,"一个新文明的到来将使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的生物局限性,并增强我们的创造力。在这个新世界里,人类与机器、现实与虚拟之间将没有明显的区别"。鉴于最近发现机器可以执行非编程或至少是无法追踪的任务(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 HI(= 人类智能)之间本应清晰的界限似乎变得不固定。
这些论点大多意味着对 “人类 ”定义的多种观点,以及各种 “后人类 ”或 “超人类 ”立场。信息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进步(人造器官、克隆、拼接、多胞胎、延长寿命等)给我们可以在生物和机器之间保持明确界限的想法蒙上了阴影。例如,非人类或后人类混合体以机器人、机器人(自动化应用)、机械人(仿人机器人)、复制人(仿生机械人)、电子人(“控制论生物”)或克隆人(基因复制品)的形式出现,为人类重新审视、重新思考、重新获取甚至重新构建人体、人体的作用及其与生物技术手段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出现了关于人类 “正常性 ”和人类特殊性的重要伦理讨论。“批判性 ”后人类主义这一经常使用的限定词,是为了标明后人类主义与超人类主义之间的区别。 一方面,批判性后人道主义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思想,总是指出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人文主义'意识形态往往只为白人、男性、欧洲顺式男性服务(参见 Hayles 1999: xiv; Vint 2007: 12; Braidotti 2013: 50)。另一方面,超人类主义对有望改善 “人类 ”的技术持积极态度,以技术乌托邦主义反击后人类学对虚假普遍主义的批判。超人类主义者可能会发展出机器适应者改善或取代人类适应者的愿景,而批判的后人类主义者可能会根据技术对克服传统上对白人、西方或欧洲人的关注的贡献来评估技术。
由于这些技术可能会改变人体,它们加剧了当前人们对后人类主义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参见 Vint 2007: 8, 182),这也与(人类)身份的概念有关。后人类机器适应者取代人类创造力的想法充满了焦虑。正如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一书中所讨论的那样,后人类论述还表明,机器总是与 “体现”(embodiment)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体现”(embodiment)清楚地表明,思想是一种更为广泛的认知功能,其特殊性取决于实施思想的体现形式"(海尔斯,1999 年:xiv)。
因此,从霍夫曼(E.T.A. Hoffmann)的《睡魔》(1817 年)、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1818 年)到菲利普-K. 迪克的《机器人梦见电羊》(1968 年),以及珍妮特-温特森的《弗兰基斯泰因》(2019 年)、伊恩-麦克尤恩的《机器如我》(2019 年)或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2021 年)等当代作品,都倾向于以人形机器人的形式来讨论人工智能。
机器越来越多地执行我们认为是人类特权的创造性任务。人工智能系统在特定应用(“专家系统”)和使用 “老式人工智能”(GOFAI)的系统(即基于符号和规则的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里程碑式成就。这种弱型(狭义)人工智能帮助 DeepBlue 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击败了加里-卡斯帕罗夫(1997 年),并逐渐通过深度学习架构得到增强,从而在更多备受关注的表演性赛事中胜过人类专家,如在 Jeopardy(IBM Watson,2011 年)和围棋(AlphaGo,2016 年;见 Heßler 2017 年)等游戏中击败人类专家。
人工智能应用模拟了人类的创造力,但它们并没有与生活纠缠在一起,没有经历过人际交流和情感接触,无法投入或冷漠、参与或脱离、愤怒或冷静。大型语言模型的创造性损害了准确性和偏差问题。
最近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最引人注目的进展影响到了语音识别或语音到文本(STT)、语音合成和文本到语音(TTS)、语音生成(如 GPT)、图像生成和文本到图像应用(如 DALL-E)以及机器翻译(如 DEEP-L)等领域。这些应用大多在平台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规则下运行(Srnicek,2016 年),由谷歌、亚马逊、Twitter/X、Meta 或微软等少数几个全球参与者监管数据访问,OpenAI(因是专有平台而被误称)是当前的技术领导者。虽然人工智能艺术经常得到主导人工智能产业的企业的赞助,但也存在对数字平台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抵抗(Zeilinger 2021: 13)和反制计划(Schönthaler 2021: 327)的情况。
带有聊天机器人界面(ChatGPT)的大型语言模型(GPT-4)已经变得如此熟练,以至于人们开始认真讨论我们是否已经接近人工通用智能。尽管许多国家都在考虑对人工智能工具进行监管,但意大利已成为第一个暂时禁止 ChatGPT 的西方国家。最近布莱克-勒莫瓦恩(Blake Lemoine)的案例很有启发性。
ChatGPT 等预先训练好的大型语言模型(LLM)中答案的正确性是纯统计学的,因此它们听起来是可信的,但由于缺乏统计学以外的推理和知识,可能仍然是不正确的,从而导致简单数学、常识推理和关于世界的事实信息的失败,而它却没有办法进行验证(Bang 等,2023 年)。这种效应通常被称为 “幻觉”,因此不应将完美预测句法中下一个单词的能力误认为是超人的智慧或创造力。克服这些缺陷的两种方法是:(1)扩大数据资源;(2)利用对话交流中出现的数据探索 “人反馈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
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人类迫切需要将模仿人类行为的机器拟人化这一事实。巴罗描绘了一只名叫 “尼珀 ”的杰克-罗素梗犬,它听着上发条的碟式留声机并歪着头,这幅画后来成为 “主人的声音(HMV)”品牌的一部分。这里的 Nipper 代表人类的反应,而留声机则是语言模型 GPT-4。在一条 Twitter 消息中,布林约尔松(马库斯 2022 年作品)认为: “就像留声机一样,这些模型利用了真正的智能:大量的文本语料库被用来用统计学上可信的单词序列训练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