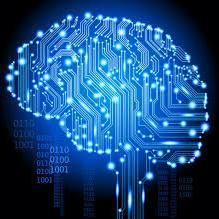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关系的新释——基于技术现象学“人性结构”的视角
| 全文共11572字,建议阅读时长11分钟 |
本文由《电化教育研究》授权发布
作者:杨绪辉 沈书生
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再一次兴起,为信息化教学模式与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教育工作者亟须一种崭新的视角和特定的语言促使教师深入理解自身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关系。首先,研究借用技术现象学“人性结构”的相关理论,解读了信息化时代教师存在的“缺陷”,剖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代具”作用;接着对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延异运动进行了解析,描摹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阶段两者关系的微妙变化;最后,对教师如何审视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关系进行了反思。研究表明,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事实上构成了“人—技术的存在结构,在后者构建未来教育空间的态势下,教师要想生存,就需正确认识人工智能技术的作用以及自身“变”的特点和趋势。
关键词:教师;人工智能技术; 人性结构;技术哲学
一 、引 言
人类正在迈进人工智能时代。由于近期在自动驾驶、语音识别以及体育竞技等领域的惊人表现,人工智能技术受到了教育工作者的极力推介,这为信息化教学模式与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构成了严重挑战。虽然广大学者正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结合点,期望为教师的教育实践提供“藤蔓”可攀;但是前两次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性影响的誓言以失败而告终,加之教育中哗众取宠的“技术”不胜枚举,教师已经深受其害,当我们再一次规劝教师,向其诉说这轮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变革的意义,描绘未来美好的图景时,语言却显得空洞无力。由此,我们亟须一种崭新的视角和特定的语言来描摹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引导教师正确看待人工智能技术的意义与价值。
二、技术现象学视角下人与技术关系的探讨
对教师和人工智能技术关系的探讨,其本质就是来看待人与技术的关系。这虽是技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将其上升为“人性结构”阐述的是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他吸收和发展了生物学家勒鲁瓦·古兰(Leroy Gourhan)的“外在性思想”,重新思索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原创性较强的技术哲学思想。
斯蒂格勒认为,动物与人类遵循着两种不同的进化模式,前者的进化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基因,其依据对环境的适应性来保留和剔除基因记忆,从而实现种族生成的过程。人类也会在生存过程中获得记忆,但是大多数记忆并未写入基因(因为1万多年前的晚期智人与现代人的生物种系特征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是通过技术将其沉淀于物质材料内,形成工具、机器等技术物体,以及语言、伦理、文化等技术体系[1],通过“馈赠”到余生和后代中的方式来维系种族的进化。这些技术物体和技术体系就保存了人类的后种系生成记忆,即技术就是人类的记忆。所谓后种系生成记忆是指物种在后天与环境的适应过程中所习得的记忆。
技术何以能够承载人类的记忆,推动人类的进化呢?斯蒂格勒则上升到“人性结构”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最初的人是先天的缺陷“存在”,即不具有完全的自然本性,人必须不断地发明、实现和创造自己的性能[2]。人为了完善自身的性能不得已借助技术进行补救,因此,技术在人的“存在”中充当了“代具”的角色,逐步使人的“存在”沦为技术性的“存在”。其中“代具”的本意为替代人肢体的器具(假肢),在这里意指人类对外在技术的强烈依赖性。也就是说,技术这一“外在的东西”构成了人的“自身存在”,从而也就意味着“人”最终是以“人—技术”的方式“存在”。正是这种存在结构和人不断补缺的诉求,使人在与技术的延异(Différance)中生成和延迟,从此踏上了“时间—历史”的进化道路。
斯蒂格勒对人性结构的阐述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其新颖的思想观点以及独特的论证方法冲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藩篱,标志着当代技术哲学对人与技术关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水平、新境界[2]。卡西尔[3]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技术对人而言,真可谓是一种天然的激励力量,激励人们实现自身本真的存在。吴国盛[4]也试图把技术阐述成人的存在方式或者“存在性差异”,从而构建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技术存在论。当我们苦恼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窘境,困惑于如何引导教师正确看待其所具有的价值,特别是描摹两者之间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帮助教师与其建立合理的关系时,斯蒂格勒的人性结构理论给了我们很大启发。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的存在结构解析
斯蒂格勒对“人—技术”人性结构的解读来源于人的“缺陷存在”和技术的“代具性弥补”。那么,对于教师这个职业而言,能否被看作一种缺陷的存在,技术又能否为其充当代具呢?冯建军[5]认为,教育活动存在着一个“主体—客体—主体”的交往过程,其实质是教师借助语言、文字、设备等技术物体的中介作用创建一个文本,学生则需要与文本达成共识以产生推动自己身心发展的内在动力。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和学生都是教育自有的,作为客体的语言、媒体、环境和教育内容都是技术或者说是由技术所创建的[6]。从这个意义讲,教师是一种缺陷存在,且必须借助技术这一外在代具来实现教育意图的传播。由上可知,教师的存在结构也可以看作“人—技术”的结构。那么,人工智能技术能否成为构建教师存在的“技术”,也就是说其与“教师”能否互构成为教师存在的“人—技术”结构。根据斯蒂格勒的理论,我们可以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即在信息化时代教师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缺陷,而人工智能技术能否作为其“代具性的弥补”。
(一)解读信息化时代教师存在的“缺陷”
脑科学实验表明,人脑认知的基本单位是知觉组织形成的“知觉物体”[7]。例如,当教师的视觉系统注意到一位行走的学生时,它所注意的是这个学生的整体(即一个知觉物体),而会忽略其身上携带的大量细节信息。这种对大量信息“视而不见”的现象正是源于人脑工作记忆容量的有限性。只有当人脑对知觉物体进行后续处理时,才会通过经验知识和上下文关系把忽略的部分弥补过来,进而形成和其他神经放电一致的联系,达成对整个事物的认识。人脑的这种工作机制不仅形成了人类认知和学习的生物学基础,也是联想和创造力生成的主要原因。然而,人脑对信息的加工不都是顺畅的,例如,如果外部世界所携带的信息量过大,知觉组织就无法完成 “瞬脱”工作,大脑接收的信号就会超出其记忆容量,后续加工过程就会受到抑制;再如,如果信息的意义不能被理解,人脑不仅无法将先验知识与信号本身的意义进行关联,还会产生一些零星的、散乱的神经放电,扰乱加工的正常秩序,使其变得烦躁。
教育中的传统技术更多的是物化形态的技术,接近于自然意义上的器械,其所承载的知识量和理解难度并未给大脑的信息加工造成过重负担,教师对技术的操作和经验的积累较为容易。然而与传统技术相比,现代信息技术所承载的知识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特质。吴国林[8]就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将技术概念扩展到了非物质的生产领域,技术的知识性意义在当今时代更为凸显。这是因为现代信息技术融入了高度理论化的科学知识,其自身所承载的规则、理论等技术知识繁多,体系结构复杂。当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内容进行整合时,教师还需对原有封闭的技术知识进行解构,根据教学需求对技术规则和程序进行重新建构,以保证教学的有效性和技术操作的流畅性,可以说是进一步扩大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复杂性。教师在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教育应用进行自主研究和学习时,无疑超出了大脑认知的信息负荷。
此外,作为“科学技术”形态出现的现代信息技术还具有另外一个特质,即技术知识的高隐性。从方法论来看,科学是人们认识和分析世界的一种方法,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使得人们对技术的判定标准发生了转向。教师对传统技术有效性的判定经常使用“真假值”,即这个技术对教师而言要么是有效的,要么是无效的;而对现代信息技术有效性的判定则是对教师意识、观念、行为和能力的透视,即教师的哪些做法促使或阻碍了技术效用的发挥。循此,现代信息技术包含了大量的隐性知识,其具有高度个体性和非理性的色彩。由于这些经验不易被他人理解,大脑就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加工,从而极大阻碍了教师之间对技术知识的交流、传播和共享。
正是由于大脑的生理局限,教师在学习现代信息技术知识时将其有效纳入到机体的图示或结构中较为困难,也很难从教师同行那里直接获取有效的经验。当教师的注意力长期离开教育本身,将注意力下放至现代信息技术,久而久之必然会给其带来烦恼,技术也随之会成为教育的障碍[9]。实际亦如此,正是由于教师对现代信息技术知识习得困难,无法解决技术性难题,从而使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紧张、害怕和畏惧等心理反应,当这种情绪弥漫于教师群体时,就会把他人“出丑”的经历移植到自己身上,进一步加剧自己的恐慌[10]。在传统技术时代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技术恐慌,但是在信息化时代,这种恐慌无疑被急剧放大了,成了教育教学中一个突出存在的问题。因此,大脑的生理局限成了信息化时代教师存在的一种“缺陷”。
(二)剖析人工智能技术的“代具”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也属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范畴,然而在智能化程度方面有着本质的提升,其主要是用来形成人工智能产品。所谓人工智能是制造智能机器的科学和工程,表现出与人类行为智能相关的特征,包括推理、学习、寻求目标、解决问题和适应性等要素[11]。事实上,用于教育的人工智能已经出现,在绘画创作、语言教学、几何练习和体育训练等领域开始崭露头角,成了教师偏爱的一种新选择。从扮演的角色来看,人工智能与以往教辅工具一样都是助力教师完成教育任务的手段,但是从工作机理来看,它们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当前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典型代表“智能评测系统”和非智能化的评测系统一样具备学生作业批阅的功能,都可以减轻教师的工作量,然而前者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使其具备语义理解能力,使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和语料库基础技术使其具有学习和思考能力,它不仅能够对学生论文式的作业给出有效的反馈,而且当评价有误时还会吸取教训,以改进下次评价的准确度[12],但后者只是将学生答案与数据库数据进行匹配进而实现封闭性评价。
尽管教育人工智能的种类很多,功能也有所区别,但是当前它们的工作原理几乎相同:开发人员提供某个教育领域的知识库,智能机器利用归纳、预测或直推等数学模型不断“训练”,以形成应对各种复杂情景的能力。智能机器的这种学习能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它能够模仿人脑神经细胞的激活模式,根据训练样本的共性特征及个性化差异进行信息提取和编码,并将其记忆到庞大的参数集中,当面临新的未知问题时就可以利用这些先验知识进行准确的预测。换言之,当研发人员提供的训练样本到达一定数量级时,智能机器就会将这一领域积累的最丰富和全面的知识与经验转化为自己的先验知识[7]。那么职业棋手李世石九段败给“阿尔法狗”就不足为奇,因为他遭遇的几乎是围棋领域“人类”的智慧。同理,一个成功的智能机器往往会超越一位优秀教师的智慧。
任何一种“缺陷存在”,为使自身的性能完善起来,必然内在地包含着“补缺”的诉求,会借助外在代具来构建自身完整的存在[6]。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电脑”无论从接受的信息数量,还是从对经验知识的学习来看,都会有着人脑无法比拟的优势。当教师面对现代信息技术洪流逐渐凸显出大脑的缺陷时,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考核监督和教师自身对教育质量追求的补缺动力作用下,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其提供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成为教师“代具”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为:由于智能机器高度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当教师熟练其操作技巧时,它会进一步呈现出透明性,即教师感觉不到技术的存在,就像是自身的生理器官一样,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如海德格尔所言,犹如上手之物在使用中的撤离,这时的技术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存在于“此在”中[13]。这表明形成具身关系的智能机器与教师之间已经合为一体,或者将其称为教师有机体的一部分更为恰当。
在信息化时代,教师大脑的生理局限阻碍了教育质量的提升,而人工智能技术有着弥补教师这部分缺陷的潜力,能够帮助其实现对现代信息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利用。从结构上来讲,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教师的“缺陷”提供“代具”作用,帮助教师成为完整的存在,因此,它们能够构成教师存在的“人—技术”的结构。
四、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延异运动
由于教育有着强烈的发展诉求,处于其中的教师也永远处在补缺和完善的状态中,因此,在对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关系进行审视时,只从静态的存在结构角度来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对其运动状态和作用机制进行探索,这对教师进一步正确看待人工智能技术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在斯蒂格勒看来,“人—技术”的人性结构在说明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时固然重要,但“人性结构”存在的前后错动、相互交融的延异方式更能说明两者的微妙关系。所谓“延异”(Différance)有两层含义,一是时间上的“延”,表示事物的“要求”和“实现”在时间上的推迟;二是空间上的“异”,表示事物之间在空间上的差异。“延异”是由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从法语词汇“Différence”改造而来,导致延异既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声音,也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文字,它既非此亦非彼,作者意在说明延异运动的缄默性和对具体事物的超越性。斯蒂格勒借用“延异”概念来说明“人—技术”的结构内部是通过“迂回”方式结成互相牵制、却具有传导关系的联合体,这种力量无声却异常强大。在对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关系进行审视时,我们可以借用“延异”理论进一步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
回望过去,在视听教育时代的末期,为了摆脱二战时期所遗留的人才填鸭式培养问题,如何实现“个别化教学”成了教师在教育工作中关注的重点。1950年,马文·明斯基等人建造了第一台神经网络计算机,其所拥有的感知能力是之前黑白电视和有声电影等任何一种视听媒体所不具备的,在此后的16年时间里,以感知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被逐步应用于数学和自然语言等教育领域,以帮助教师解决代数、几何和英语等教育问题。从该段历史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技术较于其他技术而言表现出了代具性的超前,由于教师“补缺”的需要,使得这项技术对于教师存在结构中的“人”而言表现出了空间上的“偏离”,而教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跟进,则呈现出了两者互构过程中时间上的“延迟”。这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属性与力量逐步向教师转移,两者开始从“背离”转为“相融”。
然而技术并非“教师”所自有的,它存在于“教师”之外,有自身完整性的规定,当技术构建教师的存在呈现出“疲软”姿态时,就会使技术教育化过程显现出来。其根本原因在于,技术不断构建教师的能力,进而使其发展出新的“补缺”诉求,而教师的“补缺”诉求又天然地规定着技术的属性,如果技术不符合要求,那么就要人为地改造技术,或者将不符合要求的技术要素排除在“人—技术”的结构之外。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算法、计算机性能和数据样本问题,智能机器不再能够满足教师进一步对教育高质量的追求,甚至还会出现很多“愚蠢”行为。正是由于构建教师“补缺”诉求的“疲软”,其生存空间逐步被不具备智能性的教学程序所代替。在当时除了用于构建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简单算法被保留之外,大多数的人工智能技术被排除在教师的选择意愿之外。正是由于教师诉求所形成的超前动力,人工智能技术开始新一轮的技术教育化运动,教师的实际需要开始注入其进化过程,其中算法、计算机性能和大数据成了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关键要素。
时至今日,以卷积神经算法为代表的人工神经系统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等诸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为代表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分布式并行计算技术的进步所形成的强大计算力,加之大数据技术为人工智能机器的训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测试样本,人工智能技术在技术教育化的运动下对教师又体现出了某种超前性,成了当前弥补教师大脑缺陷必不可少的“代具”。那么,可以想象新一轮教师被 “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和影响的时代即将到来。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此做的准备也证明了这一点,2016年,美国政府发布的《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等报告就明确指出,教育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已受影响的领域之一,教师需要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影响;我国国务院于2017年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提出,综合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探索未来教育教学新模式。
由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代具性“超前”,教师现有的“人—技术”结构便会表现出时间性的“推迟”,因此,教师就会处于对人工智能技术“超前”的“跟进”中,从而留下自己的时间性、历史性的足迹。一方面,从以往的经验可知,这段互构的过程可能需要经历较长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在这段历史达成之前,两者之间还会不断发生着若干轮“相互往返”的迂回运动,其间也伴随着交融。在此过程中,教师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延异中生成和延迟,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师的延异中得到发展和进化,从而让教师能够不断扬弃自身的力量,实现自身的升华。当这轮历史完成时,教育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还会产生新的变革,教师仍旧会凸显出新的缺陷,从而会推动新一轮的技术发展的浪潮。那么,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力是否会被透支,是否代表今后那个与教师形成往返的“技术”呢?
虽然未来未至,我们却可以根据人性结构及其延异的理论对人工智能技术“存在之命运”进行大胆推测。已有证据显示,由于教育人工智能运算机理的复杂性,教师很难理解智能机器给出的每个“解答”,在将其运用于教育时往往出现“不求甚解”的现象。假设未来人工智能技术足够完善,给出的“解答”足够准确,那么教师为了进一步追求高质量的教育,势必会寻找一种能够将人工智能的“解答”转化为有效操作的“代具”。在这种情势下,集“真正推理”和“解决问题”为一身的“强人工智能”或许会登上教育的舞台。“强人工智能”的构建原理与当前人工智能有着天壤之别,它是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具有知觉和自我意识,可以独立思考、制定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并能够处理前所未见的细节。不难想象,届时教师对强人工智能发展的内在诉求,还会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精进,其与教师的延异运动还会持续。虽然由强人工智能所引发对人类“有益”或“有害”的哲学思考不绝于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革命即将或者说已经开始。
五、结论与反思
借助“人—技术”的人性结构以及相互之间的延异运动,我们可以窥见到人工智能技术是弥补教师大脑生理缺陷的一种有效“代具”,在教师“补缺”动力的推动下,两者势必会互构成为教师的“人—技术”存在结构。在未来离开人工智能技术教师就不存在,因为教师职业的延续需要人工智能技术已为前提。反之,离开教师,教育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就不存在,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存在需要教师不断被激发的诉求作为超前动力。因此,在教师存在结构的内部,“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是需要在彼此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进化和发展的。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超强的潜力以及人性结构内部的延异运动,使得教师在未来较长时间里都会直面其带来的挑战。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未来教育空间的态势下,教师要想生存,就需正确认识人工智能技术的作用以及自身“变”的特点和趋势。
在审视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关系时,我们就意识到:未来在“教师”出场时,“人工智能技术”必然已经在场。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技术不是教育领域中那些只具有过渡性质甚至只是“哗众取宠”的技术,恰好相反,它具有革命性的价值和意义,是需要教师守护和负责的,与之建立联合的、构成自身的存在之物。因此,教师既不可忽视其存在的客观性,也不可诋毁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同时不要盲目虚夸其功效,造成跟风式的野蛮蔓延。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立足于“教师”之外,教师需感知到自身的“缺陷”并产生一种“补缺”诉求,才能够进一步与其形成双向互动的过程。如果将两者强行捏合,教师不仅会缺乏与外在技术互动的张力,甚至会对其产生排斥和恐慌的负面效应。
在技术现象学视野下,教师的“人—技术”存在结构意味着教师既存在于自身之内,又存在于自身之外的技术。由于技术有着自身的进化动力,且对“人”表现出“代具性”的超前,存在于自身之外的“教师”要返回自身,势必要产生“跟进”的运动,这就天然形成了自身“变”的特性,正是由于这个特性引发教师存在结构中的“人”与“技术”之间的前后交错,从而使教师具备了变动不居的品质[6],这也是教师专业发展贯穿于整个职业生涯的根本原因。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知识的产生与传播方式以及教育教学都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对教师专业思想、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等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要求更为急迫,若教师能参透自身“变”的意义与价值,势必会为不断构建和革新自身存在生成不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陈明宽.外在化的技术物体与技术物体的个性化——论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内在张力[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35(3):63-69.
[2] 郭晓晖.技术现象学视野中的人性结构——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述评[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25(7):37-42.
[3] 沈国琴.卡西尔的技术哲学思想初探[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38(3):66-71.
[4] 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
[5] 冯建军.当代主体教育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107.
[6] 叶晓玲,李艺.论教育的“教育—技术”存在结构及其中的延异运动——基于技术现象学观点的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3,34(6):5-10.
[7] 龚怡宏.人工智能是否终将超越人类智能——基于机器学习与人脑认知基本原理的探讨[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7):12-21.
[8] 吴国林.量子信息技术及其意义[J].哲学分析,2017,8(5):18-30,196.
[9] 叶晓玲,李艺.论教育中技术的生存历程及其发展指向——基于人技关系的分析与刻画[J].电化教育研究,2017,38(2):19-25,52.
[10] 覃泽宇.教学技术恐惧的内涵、生成与化解[J].中国教育学刊,2017(8):78-81.
[11] 杨现民,张昊,郭利明,等.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难题与突破路径[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8(3):30-38.
[12] 闫志明,唐夏夏,秦旋,张飞,段元美.教育人工智能(EAI)的内涵、关键技术与应用趋势——美国《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报告解析[J].远程教育杂志,2017,35(1):26-35.
[13] 李美凤,李艺.从教育与技术的关系看教育学与教育技术学的对话[J].中国电化教育,2008(1):6-10.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From Perspective of "Human Nature Structure" ofTechnological Phenomenology
YANG Xuhui1, SHEN Shusheng2
(1.Education Scientific College,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300;
2.Education Scientific Colleg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4)
[Abstract] The ri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novation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modes and methods. Therefore, educators need a new perspective and specific language to enable teacher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Firstly,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defects" of teachers in information age by using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structure" of technological phenomenology, and explains the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s a "substitute". The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érance movement between teacher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describes the subtle changes of their relationship in the past,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Finally, this paper reflects on how teachers examin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study shows that teacher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ctually constitute the existence structure of "human-technology". And if teachers want to survive, they need to form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at constructs the future educational space, and recogni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ir own "changes".
[Keywords] Teach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tructure of Human Natur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基金项目: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知识建构视野下创客教育教学模式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8YJC880106); 2018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课程视角下的创客教育探究”(项目编号:2018SJA1607)。
作者简介:杨绪辉(1986—),男,河南新乡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信息化教学设计、智慧学习环境的研究;沈书生,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转载自:《电化教育研究》 2019年 第5期
排版、插图来自公众号:MOOC(微信号:openonline)
新维空间站相关业务联系:
刘老师 13901311878
刘老师 13810520758
邓老师 17801126118
微信公众号又双叒叕改版啦
快把“MOOC”设为星标
不错过每日好文☟
喜欢我们就多一次点赞多一次分享吧~
有缘的人终会相聚,慕客君想了想,要是不分享出来,怕我们会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