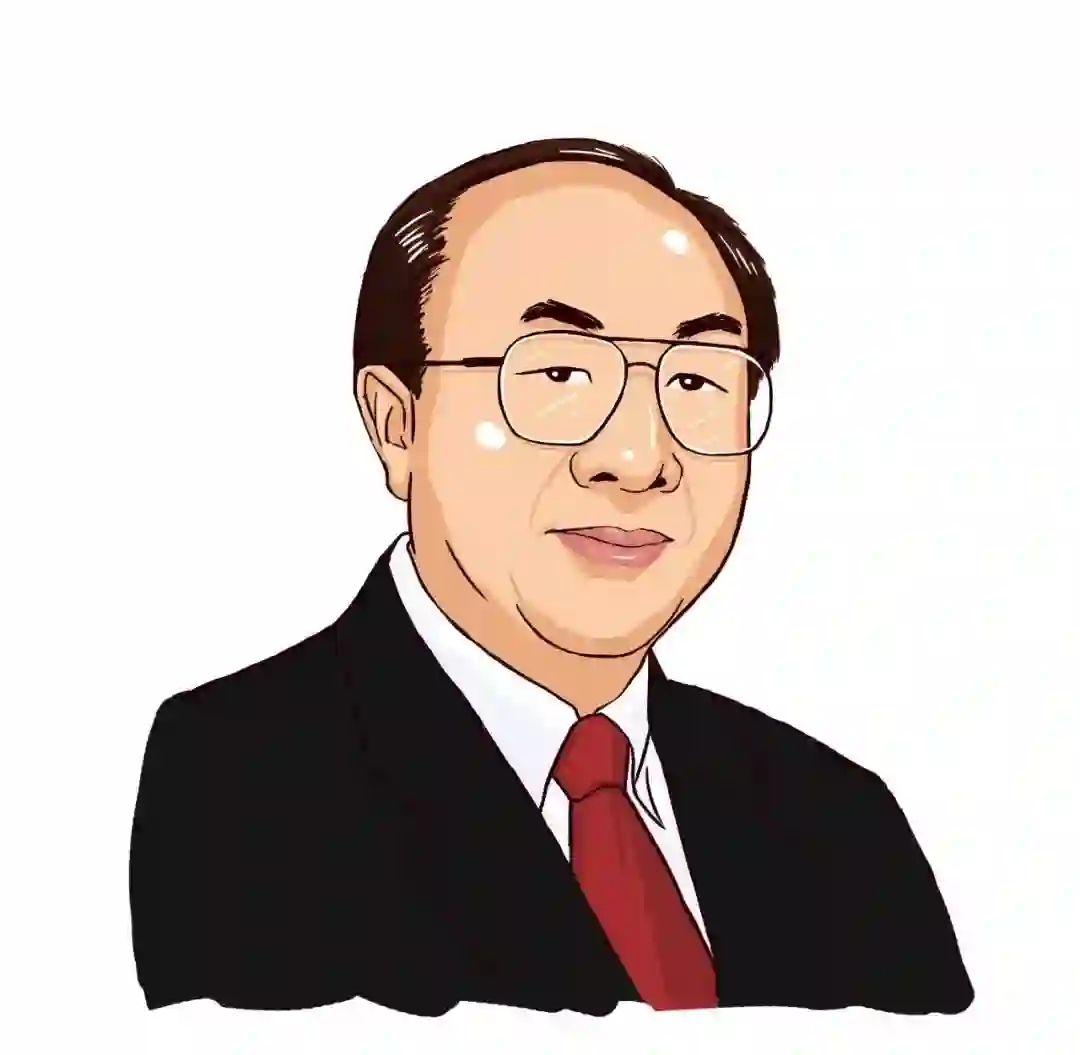前澳门大学校长赵伟教授:计算机科学的未来和素质教育的发展
赵伟介绍:1977年本科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1983和1986年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先后获得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美国阿默斯特学院、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和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协会会士(IEEE Fellow),在分布式计算、实时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和网络安全等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领导的科研团队获得多项荣誉。2006年,在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计算机与网络系统分部主任期间,领导学术界定义了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s)的概念, 投入资金启动了这方面的科学研究。2011年被中国科技部委任为国家973计划物联网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鉴于在科学与高等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赵伟被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被中国计算机学会授予“海外杰出贡献奖”,被全球十二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也是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院士。
2008年至2018年任澳门大学第八任校长。此前曾先后担任过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理学院院长、美国NSF计算机与网络系统分部主任、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分管科研的资深协理副校长。
赵伟曾在多个国家的高教科研领域任职,在教育界,从助理教授升至讲座教授;在行政管理方面,先后担任系主任、院长、副校长、校长乃至政府有关部门的司长……像他这样大幅度的跨越和丰富的经历在高教科研领域非常罕见。
自2008年赵伟担任校长以来,澳门大学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在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大学之一。
以下为《计算机教育》杂志奚春雁主编(下面简称奚)对即将离任的赵伟教授(下面简称赵)的专访。
注:赵伟已任阿联酋沙迦美国大学科研总监(副校长)。
计算机概念的变化
奚:“计算机科学”这个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至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计算机系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您认为这个概念本身是不是也发生了改变呢?
赵:这是一门很好的科学问题。 虽然计算机科学是一个科学,但可能您的有些读者还说不清,计算机科学的定义是什么,计算机到底是什么样的科学?
计算机科学确实是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当时是几个鼻祖式的人物,像克鲁斯(Knuth),他们确定计算机科学就是算法的科学。为什么到了20世纪60年代,我们就可以定义计算机科学了?其实这背后有两件事情。
第一是搞数理逻辑学者经过多年的工作,已经可以把计算和逻辑说得很清楚了。我想现在学计算机科学的一年级同学都知道,任何一个计算问题,都可以变成一个逻辑的推导问题,而且逻辑推导只有3种基本的操作,就是“与”“或”“非”,英文叫“and”“or”“not”。这不是我们搞计算机的人发明的,这是人家数理逻辑学家的成绩。
第二是搞物理的人(或者说搞电子工程的人),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现,如果逻辑推导只有“and”“or”“not”就好办了。因为这3个操作都可以用非常可靠的电子线路实现出来,而且这种电子线路就基于半导体技术。具体来说,是基于一个极简单的物理现象叫PN结现象。
归纳起来,PN结导致了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给我们提供了硬件物质基础。这两件事情的完成,为现代计算机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于是,我们搞计算机科学的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提出了计算机科学就是算法的科学。这在人类科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过去的科学,比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都是跟实物相关,而计算机科学是跟思维相关的科学。因为算法本身是一个思维的过程,程序是来实现算法而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计算机科学是非常伟大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搞计算机科学就这么说。
确定了计算机科学的定义以后,我们创造了许多的算法,接着又想了很多办法,来把算法实现得更好、更快,叫它运行得更可靠、更方便。从60年代到现在,计算机科学界的主要理论工作就是开拓了计算复杂性理论。
具体来说,是把计算问题分成两类,一类是比较容易的,一类是比较难的。所谓容易的就是有多项式算法的计算问题;比较难的就是所谓的NP问题。这是我们搞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大贡献,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创造出了许多(实用的)算法,而且我们还可以对计算问题就其算法进行分类,我们知道哪些问题计算机算起来比较快、比较好、比较适合,哪些问题我们算起来可能比较慢、比较狼狈。这个理论基本上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很成熟了。后来主要是在各个行业的应用,体现在很多方面,也涉及不同领域。
程序是数据加算法
奚:您多次获得科学和教育的终身成就荣誉,也在这方面做出很多研究和思考。想请您谈谈计算机科学发展的前景是什么?
赵:首先,大家现在比较多地在谈大数据,其实我们计算机界老祖宗本来就讲过,程序就是数据结构加算法。如果只有算法而没有数据,这本身就是不完整的。那么这个数据归不归计算机科学来研究呢?按照计算机科学的定义,它是不归的,因为我们是算法的科学,但是我认为数据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绝对是一对孪生兄弟,关系亲密分不开的。如果我们对数据很不了解,就很难进行高效的处理和计算。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侧重于搞算法,我们或多或少忽略了数据。但现在大数据来了,我觉得数据科学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亲兄弟,或者孪生兄弟,应该要推动它的发展。数据科学应该是以数据为对象,研究其内在规律。不是说计算机科学这个概念要改变,而是这个计算机科学旁边又出来了一个数据科学,就像有了物理以后,又出来化学一样。
有人可能要问:没有数据科学,我们计算机科学也发展得很好,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一定要发展数据科学吗?好像此话有道理,但是想一想其他科学的作用。比如,物理科学的形成也是最近几百年的事,而人类已经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了几千年。没有物理学,人类也有许多成就。比如,我们中国人两千年前就建造了伟大的长城。但是应该承认,有了现代物理学,人类的创造更多更新更好:我们有了电力、飞机和手机,等等。两千年前要是已经有了物理学,我们的长城一定建得更快更好,孟姜女哭长城可能就不会发生。同理,可以想象,如果有了数据科学,我们对数据的处理和应用一定会更多更快更好。到时候,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的数据处理方式一定是很笨很原始。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向是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s,i.e., CPS)(点击查看“美国21世纪CPS教育报告简介”)。在一个信息物理融合系统中,计算和物理过程高度融合,具有非常广泛的实际应用。所谓的物联网恰好就是链接各种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网络,就像互联网连接众多的计算机一样。信息物理融合系统这一新领域涵盖了传统的一些领域,诸如实时系统、自动控制、嵌入式系统,等等。自从美国NSF在2006年注资启动信息物理融合系统方面的研发以来,主要的工作侧重于应用。相应的理论工作还远不够成熟。事实上,由于涉及物理过程,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已经不再是图灵机的等价品。那么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基本的模型是什么?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就很少有人问津。
但这还都只是小戏,大戏在哪里呢?我刚才讲了,我们计算机科学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数理逻辑学家把数理逻辑和计算讲清楚了,是因为物理学家发明了半导体技术,能够支撑我们的硬件实现,也就是说,一个小小的PN结就是我们今天整个信息技术的物质基础。
最近可能大家都听到量子计算。对于一个计算机专业的老师或者学生,研究量子计算会觉得很难。我自己看过很多次,总觉得难度很大。难在哪里?是什么地方让我们搞不懂呢?后来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量子计算,它不再依赖于PN结来进行计算,它重新定义计算这个概念,它用更广义的物理的现象来支撑计算。过去我们靠PN结来支撑逻辑推理,就导致了如此轰轰烈烈的IT工业。那么现在量子计算来了,它跳出了基于PN结的简单逻辑推理,它广义地把计算看作物理系统状态的转化。
举一个通俗点的例子,这个听起来很玄妙。比如说,我要扔一个球出去,我要知道这个球的轨迹和这只球要跑多远。如果我们搞传统的计算,那么可以根据牛顿力学的公式,根据这个球的质量等去计算半天,而且这个计算结果也不是精准的,因为这是一个连续过程。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去算,算这个ΔX再算下一个ΔX,一点点算过去。大家可能都做过这种练习,但其实你想这么做多笨啊。我只要拿个球去扔,这个球在空中划的线就是轨迹,落了点就是距离,我去测就好了。这样一来,这个计算轨迹的问题就解决了。当然真正的量子计算,比我说的要复杂很多,但是它的基本道理就是这样。所以,量子计算给整个计算领域推开了一扇很大很大的门,比PN结给人类带来的福利不知要大多少。
如果说我们计算机科学领域过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将来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届时回过头看我们今天已有的结果,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了。
留出空间做原创
奚:随着人工智能学科的呼声越来越高,智能科学、机器人科学等更多的领域也相应产生,您怎样看这些领域与计算机科学的关系?
赵:我不是做人工智能的,我不懂人工智能,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懂不懂人工智能的人,都在说人工智能,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坦率地说,我不知道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懂人工智能的。
应该说在过去20年,国内的计算机科学研发发展非常快。大家都承认这个可喜可贺的事实。过去内地的作者在比较好的国际会议和杂志上发表文章都很少,很稀罕,现在已经成为常态。国内好一点的大学(比如985大学)和美国比较好的大学相比,从论文产量上来看,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甚至超过他们。产量的确上去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来关注一下质量。具体来说,我们可能非常注重发表论文的数量,甚至注重文章的引用率这种数字型指标,但是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把心思用在积累和沉淀上面,是不是更应该千方百计地给年轻人留下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能够做出原创性的东西?
我们要提倡“原创”,提倡真正的创新。说到“Machine Learning”(机器学习)这个概念,其实原创性的“MachineLearning”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母校(UMass/Amherst)的一位老师Andrew Barto从那时候就开始研究机器学习。他默默无闻做了一辈子,他的徒子徒孙们一直做下来,现在倒是很红。
目前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给年轻人时间和空间,让他们敢于提出一些原创性的想法,而不是人云亦云。这些年这种“跟风”现象,隔两年就刮一次风,开始是云计算,忽然间漫天都是云,人人都是云计算的专家,好像计算机科学将来就是云计算了。可是这云也没有飞太久,就又都是物联网,紧接着又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不是说这样不好,其实这些敏锐的洞察精神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还要沉稳下来,搞出一些真正的原创性的东西出来。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操作系统,博士毕业以后改到通信和网络,现在开始做数据。就是说,我在40年的学术生命里,变换了两三次研究方向。这大概属于正常的。但是如果每三年就变换一次,恐怕就谈不上积累了,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原创,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培养年轻人的时候,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
好在对于我们搞科研的人来说,资源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我们现在的资源配备比原来好太多了,所以我对于中国的发展很有信心,无论是创新也好,还是得图灵奖,甚至诺贝尔奖,我觉得这只是迟早的事情。
教育要有助于挖掘潜力
奚: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依赖于创新,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是一样。那么,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制度应有哪些保障?
赵:说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那一定和科研有关。有时候有一种误解,认为做科研的目的就是为了产生物质成果,物质成果可以产业化,可以卖钱,可以发财。世界上有非常多的成功案例,特别是在我们IT行业。但是我认为科研的第一目的和第二目的都不是为了成果转化,我这么讲可能有点偏激了。但是我们如果把科研和体育做个类比,就能把道理想明白。首先科研和体育都是人类的本性,也就是说,人有追求极致的天性。姚明希望投篮投到百发百中,99都不行;刘翔跨栏,他总希望跑得更快一点,希望成绩再好一点。搞科研也是一样。我们总希望在已有的结果上,做得更好。所以我们搞科研和搞体育,都是人类的本性。我们培养学生,就是要激励学生,把人的潜在的最基本的本能激发出来。刚才讲到的原创,如果不是本能被激发的话,原创性的东西是出不来的。
第二,我们在奥运会上拿了很多金牌,全国人民为之高兴。但试问我们拿了那么多金牌,有实际用处吗?能吃能喝吗?好像不行。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凝聚人心的一个重要手段。就为了这一点,我们就是要搞体育,就是要办奥运会。其实,搞科研的目的之一也是如此。我们科研搞好了,“神九”“神十”上天了,老百姓也非常激动。但是如果非要问,这些神舟飞船马上能得到什么物质效益吗?好像没有。但是我们就是要搞神舟,就是要写好的文章,就是要在科研上做出突破;因为这是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
第三,体育和科研当然也有实用意义。搞了体育,大家的身体素质提高;搞科研有了成果,可能有实际用途,还可以商业化,等等。
所以把这些想明白,我们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制度保障就明白了。首先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前提下,无论是教育制度还是老师素质,关键就是要确保能够培养学生身上最基本的力求极致和不停探索的素质。假设今天我们上一门手机课,你若要求上完手机课以后,学生马上可以发明一种新手机,这大概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如果上手机课的时候,注重培养学生的潜在素质,他将来就很可能在其他方面有所突破,因为他的素质得到了培养,他就会追求极致。在实际当中,他就努力做得比别人好,坚持探求未知。这样的话,我们渴求的原创性的东西就会出来,就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贡献了。
转载声明:文章转载自【计算机教育】公众号。
推荐阅读
商汤获6亿美元C轮融资,与矿视的战争将如何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