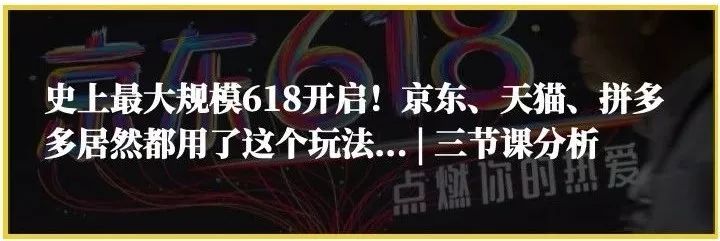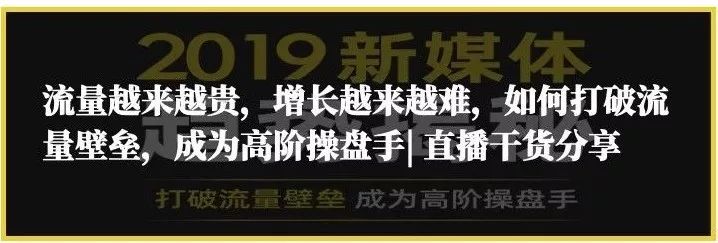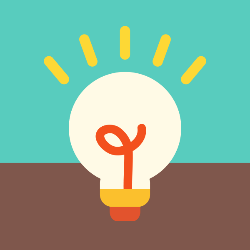了不起的创变者 | 三节课后显慧:避开风口的抉择
5月21日,三节课正式宣布完成B轮1.3亿元融资的消息。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的CEO,后显慧(Luke),接受了36氪「了不起的创变者」栏目记者的专访。
如果把三节课比喻成一艘大船,Luke就是制定航线、掌舵的船长,布棉(三节课联合创始人,徐财星)和老黄(三节课联合创始人,黄有璨)是保证这艘船能够正常航行的副船长,而我们这些员工,则是保证动力的水手们。
在这艘“大船”开启航行的第四年,借由36氪这次的采访,我们得以看见了老板们的另一面:不断互相“逼”着对方做出改变,一起走出了一个又一个“舒适区”,虽然也曾有过焦虑和迷茫,但最终还是坚定方向,准备沿着教育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正如Luke所说:创业和学习一样,对人的合成都是”化学反应“,过程很酸爽,结果我想我也会很喜欢。希望这篇采访可以给正在奋斗的你带来一些动力,在所有为梦想奋斗的路上,我们都与你在一起~
—
文 | 吴影
文章来源 | 36氪
2019年5月21日,三节课正式对外宣布获得双湖资本领投的B轮1.3亿元融资,这是过去3年来在新职业教育领域内规模最大的单笔融资。这源于创始人后显慧一次避开风口的抉择。
大梦谁先觉
2016年3月,北京西郊大觉寺,天气,不详;具体日期,没有印象;大觉寺著名的玉兰花开没开,没有人提到这一点;喝的什么茶,吃了什么坚果,统统不记得了。
那一天,后显慧(下文称“Luke”)、黄有璨、徐财星(下文称“布棉”)——三节课的三位创始人驱车40公里,决定在此讨论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
三节课在2015年年末成立,定位为“互联网人的在线大学”,在此之前,三节课作为非盈利组织已经运转了一年多。刚刚开始创业,几位创始人摩拳擦掌,“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都可以做的,这个也有需求,那个也有需求”,他们做了课程,写了公众号,还要开发产品,甚至还做了一款给用户画原型图的产品——圆规。
“当时产品路线很多,资源的消耗也比较严重,产出也不明显”,Luke回忆,半年过去,警钟敲响,“钱也花了一半以上,也没有任何迹象证明这件事是能走通的,就有点焦虑了。”
焦虑的同时,风口来了,知识付费领域频频有好消息传来。头一年年末“得到”APP上线,喜马拉雅、知乎开启了一系列新动作,值乎、分答在酝酿之中。有人找到Luke,“你们三个特别适合做知识付费,能写、能说、有粉丝,一年一千万收费是没问题的”。有的平台来找三节课开专栏,“可以给我们一些钱,音频或者图文都可以,许诺先把我们包装成IP”。
三位合伙人都有讲课的经验,往知识付费去走,讲义几乎是现成的,收入也是清晰可见的。但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也在Luke心中蔓延,“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教育。但很多人跟我说教育是很重的业务,需要花时间去练习,去打磨课程,知识付费是很快的……我们到底是做快的、顺风的,还是慢的、看不到任何机会的事情?”
那段时间,Luke醒得很早,每天早上7、8点就拉着黄有璨、布棉在会议室聊,但迟迟没有答案。在3月的这一天,他们决定换个环境,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做出这个决定。
三个男人都是30多岁,他们最早结识于黄有璨的创业项目。当时黄的团队在做产品经理线下培训,找到Luke和布棉一起开发课程,两天的培训,收费1999元,每一期都是爆满的。但在做了十几期后,他们又不约而同地离开了这个项目。
“每一次讲完用户都很开心,用户都会给我们评分,10分满分,评9.5、9.7、9.8,都有。但是每次讲完课之后,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总有之前上过课的人回来问你,说这个课听完了,我回到我公司里面,我还有好多具体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黄有璨回忆,“你出卖自己的时间,去挣点钱,这个事不像是一个很互联网的事,不像一个先进的生产力……我们对这个事的价值不太认可。”是在这个时候,三个人感觉到互相“在很多价值理念或者价值判断上高度的相似”。
在大觉寺的这个下午,“我们三个人在自己心里面画一画,写一写,现在要做什么?如果不做可能是会后悔的,它跟机会没有关系。” Luke说,不到晚饭时间,答案就出来了,“教育是我们三个人内心的梦想”。
后来这个下午在Luke的回忆中总是萦绕着这句话,“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感觉这句话很符合我们当时的心境。我们喝了一下午茶,把所有事情都抛开,并且找到了那件我们非做不可的事情,即使失败了我们也认,如果成功了就更开心。”
“瓶瓶罐罐,让它发酵”
后来就是三年后的这个下午了,接受36氪采访的3个多小时里,Luke的iWatch响个不停,都是陌生来电。这是入夏以来北京最热一天,北京局地气温高达37℃,气氛之炙热从天气开始蔓延。
采访的两天前,三节课正式对外宣布获得双湖资本领投的B轮1.3亿元融资,这是过去3年来在新职业教育领域内规模最大的单笔融资,也是今年略显冷淡的资本市场少见的好消息,Luke不得不开始了这种“迎来送往”的日子。另外两个合伙人的状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宣布融资当天,黄有璨的微信上就多了100多个好友申请。
但在成立三年多的三节课公司内部,并没有庆祝的气氛。Luke只是在公司内部邮件里向同事们通报了这个消息,合伙人在公司群里发了几个红包,这件事就过去了。“我们理解还谈不上成功,只是一个新起点而已。”布棉说。
Luke在公司内部一间茶室里接受36氪的采访,玻璃窗外阳光炽烈,他穿白T恤、牛仔裤、New Balance运动鞋——典型的互联网人装扮,语言简洁、真诚,他一次一次摁掉来电,从公司的选址开始聊起。
三节课是2018年7月搬的家,从中关村搬到北四环,紧挨着教育科学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是一个全部打通的两层小楼。Luke对行政同事提出的要求是,不要高层写字楼,“电梯很高那种楼,我觉得对于学习型组织来说是比较难受的事情,感觉高楼更适合于效率,不太适于成长、发酵的东西。你看发酵的东西,都是在大工厂里,很多瓶瓶罐罐,大地和阳光让它发酵”;他也不倾向创业公司扎堆的园区,“我们需要自成氛围,我希望我们公司就是一个氛围原创地。”
当3年前坚定了做教育的决心,Luke就很少再有大方向的迷茫。回到公司,他们立即决定将重心放在课程的打造,“这个课程要做体系化,要花时间,同时要培训这样的团队,有教研能力的团队、有教学服务能力的团队,整个产品的设计或者网站的设计按照那种沉浸式学习的方式去打造,基本上产生了因之后果就自然出现很多东西了,所以所谓的行动和决策就不纠结了”。
那个时期,几乎所有互联网创业项目都会做一个APP。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了,只有网站和公众号,太古典了,太不靠谱了。但暂时不开发APP的决定,Luke做得异常坚定,“我手里有一笔钱,我要去做APP的投入开发,还是做课程,我想我应该是做课程”;“另一方面,我们早期这样的项目,连什么样的学习形态和业务模式都不知道,我想我们应该去快速迭代找到我们的模式……APP的版本审核需要15天,速度非常慢”;“碎片化学习可以通过手机的碎片时间学习,但我们的课程是体系课程,用手机学一个八周的课程,不是更方便了,而是效率更低。”
而教育这件“慢的、看不到机会的事”,开始慢慢长出一些美丽的枝桠。“当我们决定坚持要做教育、不做知识付费的时候,我们发现用户开始慢慢认同我们的理念了,他们认为三节课的确是跟别人不一样,三节课就是体系化的,课程就是很“虐”的,学习压力就是很大的,但是大家还喜欢挑战这种学习的压力,慢慢口碑也出来了。”
黄金一代
“动作”,三个创始人在提到这轮融资时,不约不同地提到了这个词。Luke用体操项目跳马打比方,“我们去(看)奥运会跳马比赛,最后一个动作是落地,落地能不能站稳是很重要的一项评分指标,但运动员可能在那个点上很难控制,大概率可能要看运动员当时的发挥,甚至当时几天的运动状态……但是以什么样的速度起跑、一共跑多少步、在哪个点上起跳、旋转,这是基于N次训练的结果。我追求的是基本动作一定要做到位,也许很多人追求的是最后落地稳定……我觉得把动作做到位,结果自然达成,这可能是我理解的因果关系吧。”
说出这番话需要一种在当下少见的从容,而这种从容大概来源于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坚定,和互联网黄金一代所受到的训练。
Luke本科念的是国际政治,研究生师从中国传媒大学刘继南教授学习国际传播,从高中二年级看到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新闻开始,他就决定自己要成为一名国际新闻记者,但这份职业理想在进入央视实习时戛然而止,他当时担任《朝闻天下》 编导实习生,“突然发现那个工作方式,不是创造型的,是选择型的,是一个列表给到你,一些信息表给到你,你去剪好了。”
他很快去了智联招聘实习,那是2005年,第一波互联网泡沫开始消散,互联网人“很有朝气,很自由,充满了这种战斗力吧,激情,我觉得特别喜欢”,“他们也很喜欢分享和交流,总有说不完的话,大家聚在一起各种点子和想法会冒出来”,Luke深受鼓舞,他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互联网非常真实,因为当时我们大家对互联网是虚拟的,是泡沫的,我觉得互联网特别真实。”
他无师自通地开发出了一款名为“薪酬查询器”的产品,这出自对用户需求的敏锐感知,也出自一种创造的热情,“大家都希望知道说,我下一份工作应该拿多少钱”,这款产品在当时还成为一些学生高考填报志愿的依据。越往后走,他对产品开发越有兴趣,之后他先后就职阿里巴巴、百度,在顶尖互联网公司受训,“(公司)会主动加薪,而且加的还都要超过我的预期。我觉得不是我多优秀,是这个行业真的非常好。”
他的另外两个伙伴——布棉毕业自一所农学院的房地产专业,但他从1997年就开始上网,那时白天上网一小时6块,而到了夜晚,从0点到8点,也只要6块,他通宵蹲守互联网,于是给自己取的网名是“不眠”的谐音;而在贵阳一所重点中学念书的黄有璨,因为和老师一道主观题的标准答案意见不同而产生冲突,愤然退学,天天泡在论坛里,灌水盖楼,乐此不疲,这是他在2008年进入互联网行业的肇始。
“我们三个人都是方法论主义者,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这种事情,或者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至少部分可以方法论化的,百分之百做不到,60%、70%、80%大概可以做到。”黄有璨总结说,他和Luke以及布棉的关系是他觉得这次创业中“挺幸福、也挺奇葩的事”,“我还真的没有看到过一家公司的合伙人之间能够像我们3个这样的沟通和决策成本这么低”。
从2005到2015年,Luke评价自己经历的是“黄金十年”。年龄相近的三个合伙人,都曾亲身感受互联网的自由、开放与创造力,由衷地相信它。即使到了增速放缓的今天,在Luke的判断里,“我都觉得互联网的价值不存在疑问,因为它能提升生产效率,对生产力是有帮助的”,这也促成了他对于新职业教育的基底判断,“我们就相信所有的新的岗位都会出现,用人的需求我们把他解决就好了,我们为什么要今天在产品经理,未来产品经理没了电子竞技就出来了,电子竞技没了,区块链就出来了,出现新的岗位我们把这个岗位的职业教育做好就行了,我们不是很担心未来的品类限制。”
完人的过程
站在黄有璨的视角上看,Luke是从2018年开始,才算成为了一个“比较合格”的CEO。“这是他第一次创业,他也在找感觉。我自己典型不是一个CEO的这种状态,我也做不了CEO,但是我大概知道CEO的状态对还是不对……从2018年开始这个感觉就特别好。”
最初决定创业,Luke是被市场需求倒逼着出来的。念头产生在2015年的一个瞬间,那时候三节课作为公益组织已经运行了一年多。头一年时任总理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了创业热潮,一时间对于产品经理和互联网运营的需求激增,但大学不培养这类人才,三节课每周开放50个报名名额,最快的一次25秒被抢光。
苦于开课没有固定场地,全靠学员、志愿者们临时支援,常常借用他们公司周末空置的会议室,到了夏天没有空调,老师学员头顶上都在冒汗,Luke开玩笑叫“求知欲汗流浃背”。
当时Luke还在百度上班,每周末出来做培训,有时候也犯疑惑,想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得出的结论是“他们需要我”,他分析自己“内心里面有点讨好型人格”,“我看到别人开心我觉得我很开心”。
一个投资人找到Luke,说在798租了一个500平米的楼,免费给三节课使用。这栋楼开始牵动他的心,“有一天我在四环上开车,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出来创业,我就给他们俩打个电话。因为有璨有心理准备,老布没有的,一直就是开开心心的跟我们上课,无忧无虑的,我说老布我想出来创业了,我想做三节课,老布你的想法是什么?他说那我们就出来做!然后跟有璨打电话说我想出来创业,要不要一起出来做?他说行,那就出来做吧!”
Luke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动的人,就好像过去他去蹦极,是被一把推下去的,自己是被推着走到了创业这一步。但创业考验的不仅仅是热情,不仅仅是商业模式,它拷问的是人的内心。一直到2018年,他“还是希望保持一个非CEO的角色存在在公司”,新入职了同事,他觉得好像还不认识,希望对方拿他当朋友,就专门花时间去和新人聊天。
有时候黄有璨会提醒他,这些我来,你应该去看更大的事情。他意识到公司规模日渐扩大,行驶的海域越来越复杂,他要做那个掌舵的人。
在经历了一段沉默而焦躁的时期后,黄有璨和布棉都察觉到了他的变化,布棉说,“架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特别能理解,如果他不能转变成一个主动的角色的话,自然可能这个公司也只是一个平庸的公司。”
他变得沉思更多,拒绝琐碎事务更多,这间公司最早的员工晓玲说,在三节课内部,Luke每周会写一篇周报,发给全体同事,内容是他上一周思考的结果。
这是创业带给Luke的严酷历练,“这个过程是完人的过程,完美的人的过程。”
大学时期Luke就喜欢研究哲学,他最近又翻出了《康德传》,“理性是一件好事,但是人最终还是要走向非理性的,(康德)说是真善美。从感性到知性到理性,然后才到这种非理性——真善美,他叫德性。”
“一家公司一个组织,它能够从这种丛林里面走出来,要不要有肌肉?肯定当然是要有肌肉,但是只有肌肉你能走多远?不是很远的。所以需要超越肌肉这种竞争能力……就是你有一个更大格局。”
“因为做公司越来越理性了,然后理性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可能理性会把你的一些想法异化。举个例子,你要做用户,你要做收入,你要做规模,这当然是商业的要求,这是规律……所以我也在学习和感悟,试着从康德那找营养,能不能从商业逻辑里跳出来,感受到产品和课程对用户的价值,追求一些现实之外的理想。”
这是新一轮的挑战。Luke很少豪言壮语,只在2016年公司内部的一次月会说过,“这家公司非常小,就20多个人,但是它非常的不一样,现在我们看到不一样,未来也会有不一样的。今天我也是觉得说,如果它失败,那么它就是一次正常的创业失败。但是如果它成功的话,可能是不一样的成功。”这是新一代互联网人的抱负。(完)
—— / 你可能错过的精彩内容 / ——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