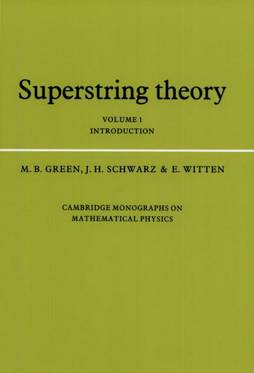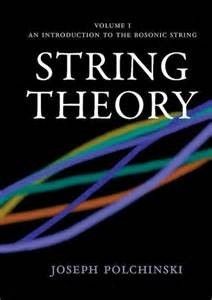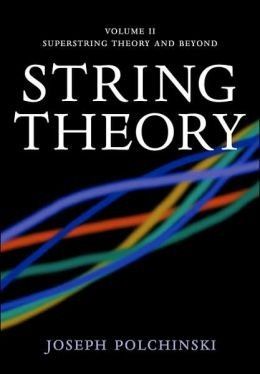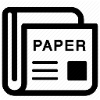《弦论》是怎样诞生的 | 理论物理学家约瑟夫•波尔钦斯基回忆录译文节选
在 1988 年的夏天,我发现我可能成不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于是我决定写一本书。
这实际上算得上是个意外。一切不都发展得很不错吗?我研究的题目很有趣,而且时常还能得到我所钦佩的人的正面评价。尽管如此,我还是没觉得我在推动科学的进步。那段时间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是发现了杂化弦与观察到的标准模型的联系,但是我却没有趁手的办法来解决它。实际上,回顾往昔的时候,我都是在处理一些看起来非常奇怪的东西,而不像那些真正的问题。在那段时间,我唯一一篇引用数较高的弦论文章是我的第一篇弦论文章,主题是玻利亚科夫路径积分,而那篇文章可以说只是一篇介绍性的文章罢了。而与此同时,其他人在做的东西看起来都会是重大的进展。
爱德华·威腾
在这些人里面,最耀眼的就是爱德华·威腾。十年来,他的新点子持续地推动高能理论界前进,就像费曼,盖尔曼,温伯格,玻利亚科夫,以及特·霍夫特曾经做的那样。我还记得,即使在弦论诞生之前,我也很喜欢读威腾的文章,并从中学到了关于量子场论的我未曾预料到的新知识。但同时他的推进又是势不可挡的。
费曼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说中讲了可怜的斯洛特尼克的故事,其博士论文被费曼在一个晚上重复了出来。并不令人意外地,斯洛特尼克再也没有写过别的文章。像这样的费曼影响了其他人的故事发生了不止一次。在前文我提到了与威腾的第一次会面,那感觉就像斯洛特尼克与费曼的会面一样。然而我觉得爱德华从不像费曼那样表现的锋芒毕露;相反的,他把他的锋芒对准了历史。尽管如此,他的每篇文章都在带给了我非常愉悦的体验的同时,还会让我进而思考:“既生威腾何生我?”
当然,虽然没那么夸张,但我可能也对我在加州理工的一些同学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但是科学毕竟是宽阔无际的,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幸运的是,即使理论物理也是很广阔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在继续讲我的书之前,先容许我对你们幸灾乐祸一会儿。我最近看了电影《莫扎特》,在我看来(可能有点不准确),这部电影讲了萨列里因为没有莫扎特的天分而饱受折磨。我对萨列里感同身受。我在我办公室的门后面贴了一副威腾的画像,免得到了见面的时候我过于紧张。(对,我就是这种笨蛋)。
GSW的弦论书
我写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刚刚教完一年长的基于玻利亚科夫路径积分的弦论课程。格林,施瓦兹和威腾,即 GSW,刚刚写了两卷的弦论书,然而他们并没有包含玻利亚科夫路径积分的内容,而是使用了以前的光锥的办法。我想,既然我这一年内的的课程笔记与 GSW 没有太大的重复,我实际上可以把它弄成书。看起来人们喜欢我的写作,而我也喜欢写点东西,尽管我没能解释写篇文章和写本书之间巨大的耗时差距。此外我一直在追求进步,而弦论也的确持续发展了九年。这段时间我每年都花了差不多 30% 的时间在我的书上,基本上都是在夏天。有一年因为 D-膜的发现,我休息了一段时间,但是第二年我就意识到我需要完成它,然后几乎把一整年都花在了写作上。
既然当了萨列里,我索性也当了次米开朗基罗。他给教皇朱利叶斯做坟墓的那些时光真是令人难堪。浪费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在这种事情上,真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直到我完成我的书后很久我才意识到我也是一 样。
我不太多的涉及这本书具体的内容了。它与我生活的其他部分,乃至研究都没有太大的交集。可能会让人惊讶的是,它甚至拖慢了我的研究进程。想象一下,它剥夺了我 30% 的时光。然而我还是很后悔,自己在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放弃了一些物理研究。我那时正在重新思考单极催化的问题,并试图完善这个理论。我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有效场论,其有效场比单极子更轻但是比其它的都要更重。我意识到这在很多情况下都会遇到,比如重-轻夸克,甚至质子-电子。所以我找到了马克·怀斯,问他是否见过这样的东西。他觉得这看起来很有意思,并认为我们应该一起把它弄清楚。然而我才开始写书,并且不想停下来,于是我让怀斯和南森·伊斯格尔去搞这件事。最终得到的的重夸克理论非常有用。怀斯因此常和我开玩笑说他在我刚到哈佛时给了我一个项目,而我则在后面还给了他。
最后说三个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史蒂夫·温伯格,他用他优美的引力论教材设定了一个标准,而我想要达到这一标准。最开始我们讨论过合作写一本书,但是我的不按照历史顺序的做法很难与他的写法融合起来。另外就是爱德华·威腾了,原因已经说过了。第三位就是简·哈格,她是我第一个孩子一岁时的贴身保姆。她这个人很有趣,曾经环游了世界,并且计划写一本自传。于是我就想着,既然我的保姆可以写自传,我当然也可以啦。
……
我有一年没有理会写书的事情,但是现在已经到了无论如何我都不得不去完成它的时候了。因此,我决定在我完成这本书前不去做任何其他事。人们告诉我在那段时间我就像一具僵尸,他们知道试图去和我交谈是没有意义的。
《弦论》卷一
为了约束我自己,我把每天要写几页写在一张纸上。这个清单在我办公室的公告栏上贴了二十年,但在写这个章节之前我从未看过它。当我去看的时候我实在是被震惊到了。在九年里,我写完了现在被称作卷一的部分——还不到整本书的一半。这和坎德拉斯的格言是吻合的,放弃写书要趁早。我想要不是我把写书这件事搞得人尽皆知的话,我早就放弃了。至少超弦革命没有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有个章节是关于超弦对偶,还有的是关于 D 膜,但在给过学术报告和讲座之后这些都变得很容易写了。之后,正好在期限之前,还写了一节分别是关于黑洞熵和矩阵理论的内容以提供一些基本的观念,最后还有一点关于 AdS/CFT 的段落,只是为了赶上最后的期限。
我在卷一上花了些时间的原因之一是,我把开始的几章重写了很多次。比如刚开始我认为 BRST 对称性可能是最核心的原理,但后来我却删减了它的内容,并把相应的东西补充到了共形场论的章节里面。我有个想法,我要写一本非常清晰的书,以至于有学生在某个夜晚拿起它后就无法放下,在第二天清晨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弦论。我从未觉得这本书好到令我感到满足,但人们似乎觉得它很有用。
《弦论》卷二
根据我的记录,在六个月里我花了 83 天进行写作,创作了卷二的 500 页:六个月里基本上每周我都有三天在写作。这还不包括对书中许多课题的研究时间,因为之前我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与这些课题相关的工作。在这期间我有三次短暂的休息,去完成了与贝克尔、贝克尔以及采特林合著的论文,与霍洛维茨合著的论文,还有与黑勒曼合著的论文。我还有一些日常生活:记录里显示曾有一次到红杉国家森林公园和克恩河的四天家庭旅行,并且我还继续给我儿子的曲棍球队担任教练。不过我很确定通常时间我依然是一具僵尸。
就是在此期间,我做出了把整本书分为两卷的决定,因为内容量的多少已日渐清晰。整部书的书名,很长一段时间就叫《弦论》。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曾用过《弦论现代导引》这样的标题,以表明使用了对玻利亚科夫描述,但我意识到很快这个题目就会过时了。不过假使我今日动笔,也依然想不出其他的写法。我还曾用过《乔的弦论大作》作为早期不正式的标题;我本应该更努力的去让这个标题成为官方的正式标题。
在完成写作后,又有六个月的苦差事:校验,检查方程,设计习题,做编辑要求的修正,写上术语,参考文献和索引。在每一步我都不得不从头到尾去检验,共有 800 页。索引至少还是有趣的,需要翻开每一页去看是否有一些东西是读者需要去寻找的。最后我终于完成了所有工作。我曾稍微降低了我“易读”的目标,也稍微降低了“没有排版印刷错误”的目标。我曾检查过每个方程,但我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关注细节的确不是我的强项,并且在 800 页包含许多环环相扣的主题的书中保持自洽的符号习惯是尤其困难的。所以现在勘误表超过了 400 个,其中至少有 200 个来自于班克斯曾经的学生卢博斯·莫特尔。最后,我计划添加一些关于超弦理论有限性的证明。我认为我已经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模掉快子后玻色弦是有限的。但那篇文献中并没有给出证明,而且在几次尝试之后我意识到,在合理的时间内证明它,已经是我无法做到的事了。的确,这个证明是在最近才被威腾在一系列长论文中做出来。
之前我提到过,因为写书,我错过了在重夸克理论上有所突破的机会。另一个是更多的和西梅昂·黑勒曼合作的机会。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例如,他现在的研讨班包括 3000 个幻灯片,以定格模式被展示出来)。我们写了两篇论文深入讨论矩阵理论,但就在他的关键时期,我不得不进入行尸走肉模式一年。他和肖恩·卡罗尔(当时是 ITP 的博士后)、马克·特罗登一起写了两篇关于畴壁的非常棒的论文。他之后去 SLAC/斯坦福和 IAS 做博士后,再后来在东京 IPMU 拿到了教职。他总是写一些新奇的论文。
我并没有回想起有过任何特殊的庆祝活动,这(完成写书)仅仅是一个回到工作并赶上所有最近令人兴奋的工作的机会。接着,我的版税开始进账了,这是一笔丰厚的报酬,但这并非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前几年,大卫·杰克逊举办了一个聚会,向我们展示了他靠他的《经典电动力学》所获得的在伯克利山上的大房子。过了一段时间,在佛罗里达,皮埃尔·拉蒙向我展示了他用他的量子场论书的版税购买的非常棒的望远镜。而随着时间流逝,我的书使我获得了一辆宝马,包括税金:价值是房子和望远镜的均方根。
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下载回忆录译文完整版。
附:前言
波尔钦斯基在圣芭芭拉
当我在治疗脑损伤并因而难以工作的时候,两个朋友(一个是来自 KITP 的朋友德里克·韦斯滕,另一个是最近与我有过合作的史蒂夫·申克)建议到选择一个新的方向可能会是个不错的主意。 Steve 特别提到我是一个很好的写作者,并建议我尝试一下。我很快就接受了 Steve 的建议。 因为我只具有两方面的知识,也就是关于我自己和关于物理的,我决定写一部关于我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的成长过程的自传。
这并不是为任何特定的读者而写的,只是为了给我自己一个目标而已。 对于一位非专业的读者来说包含的物理可能太多了,而对于物理学家则是太少了,有些部分可能会很乏味。但是,我认为它某种程度上是唯一的,是一个关于我从何开始到达何处的及其详尽的历史。
可能的目标读者是理论物理学家,特别是那些可能会乐于将我的奋斗与他们自己的相比较的年轻人。
一些免责声明:本文基于我自己的记忆,并拼接上了 arXiv 和 INSPIRE 上的记载。这里肯定有错误和疏漏。同时请注意标题:本文是关于我的回忆的,而这可能会和其他人的有所不同。此外,对我来说提及所有工作与我有交叉的作者是不可能的,因此本文不应该被当成一篇可供参考的文献。
最困难的决定之一是在提到别人的时候是用名还是用姓。但是因为名字更加难于区分,所以我会统一用姓,即使这样对于一些好朋友来说会感到不自然。
我要感谢史蒂文·波尔钦斯基和比尔·扎伊茨仔细阅读了草稿。
最后,我欠多罗茜太多了,她在四十多年里为我们共同的生活付出了 很多,特别是在此前的二十一个月中。
译序
在 8 月 31 日的早晨,arXiv 上发布了超弦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Polchinski 的自传。开篇第一句就是“While I was dealing with a brain injury and finding it difficult to work...”看到这句话,很多人都感到心情非常沉重。此前就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 Polchinski 教授被查出患有脑癌,但具体情况大家都知之甚少。而这次的自传,无疑是证实了这个消息。
Polchinski 的超弦教材是很多相关方向理论物理学工作者的入门读物。 这部精彩的著作带领很多人进入了弦论领域,而人们也爱屋及乌地对作者产生了敬佩之情。因此张建东就在某个主题是讨论数学和物理的群里提议一起把本文翻译成中文,并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随后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并拉进来很多也有相同想法的朋友,一起商讨具体的安排。讨论的结果是首先要取得 Polchinski 教授的授权。随后张建东和付子操代表翻译小组向 Polchinski 教授发送了邮件,申请获得将本文翻译成中文的授权,邮件全文如下:
Aug 31, 2017, at 13:12 UTC+8
Dear Prof. Joseph Polchinski,
We are young physics students from China who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your books and research papers.
Today we saw your memories announced on arXiv. After reading it, we were deeply touched by this article and benefited a lot from it.
We don’t know whether you plan to publish this article or not. But we would like to translate it into Chinese, and then much more people can benefit from your article. Currently, we plan to make the translated version free online.
As this article has 150 pages, I (Zhang) convened some friends who are also physics students to translate it together. One of my friends Zicao Fu is also a PhD student in UCSB. I think you may be familiar with him, so we wrote this email together.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you can ask either me or him.
We sent you this email to ask for your permission to translate this article. May we get your permission of translation?
We wish you a good health!
Thank you very much!
Best Wishes
Jian-dong Zhang, Zicao Fu, et al
很快,我们就收到了病中的Polchinski教授的回信,同意我们翻译本文,全文如下:
Sep 1, 2017, 9:56 UTC+8
Dear Jian-dong Zhang, Zicao Fu, et. al.
I am honored that you wish to translate this, and I am happy to grant permission. There is one typo that needs correction, brane cancer → brain cancer on page 150. Likely there will be others, but this one is especially bad.
I do not know at this point about plans to extend this or publish it, but I am happy that it will be read.
Best, Joe
收到回复之后,我们立刻开展了任务分配工作,将全文均分成十五部分,交给不同的人来翻译。每部分翻译完之后再分别找一个人进行校对,过程中的问题都在微信群中讨论。因为人力有限,有不少人都承担了多项任务。此外为了统一全文的名词翻译、人名地名以及语言风格,最后又进行了可能并不够完善的统稿。在缩写词是否翻译这一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因此目前完全按照原译者的方式保留。此外因为篇幅很长,所以必然在统一名词的翻译上有很多遗漏指出,这一点将会在之后的版本中进行修正。在历时一个月的努力后,终于完成了初稿的制作。翻译组中每个人的物理和英语水平也不尽相同,再加上人力有限,并且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与翻译工作,因此最终的版本必然会存在很多不足和错误之处, 还恳请各位读者的谅解。
这次发布的版本算是一个初稿,以后也会不断改进升级。这一版本基于 Polchinski 教授在 8 月 31 日放在 arXiv 上的版本,此后 Polchinski 又进行了更新修正了他发现的一些问题。因时间有限,而且版本更新时我们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部分,所以我们并没有按照最新的版本进行翻译。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只修改了一些明显的笔误,基于新版本的翻译我们会在后续升级的时候完成。目前的版本排版和格式上完全遵循了 Polchinski 教授发布的 LATEX 源文件,并使用 LATEX 编译。后续的版本除了对现有文稿的修订和校正以及排版的美化,还可能会增加诸如参考文献、名词索引、人物简介、 一些题图和插图以及一个美观的封面等内容,也欢迎各位提出相关的建议。 如果各位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问题,恳请您通过邮件告知小组负责人(地址见下段),我们将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
本文原文及出版版权归 Polchinski 教授所有,译文版权归翻译小组所有。小组负责人为张建东,如有疑问,请联系 zhangjd9@mail.sysu.edu.cn
最后,祝愿 Polchinski 教授早日康复!
2017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