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升级下的新文青时代
1
文青,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小视角。
1984年,《上海文学》七月刊收录了短篇小说《棋王》,一经刊出,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阿城便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坛新星。他走红的程度,大约相当于1986年的崔健,或是1992年的张雨生,各大刊物的编辑慕名前来求稿。阿城好客,消耗了大量的茶叶和挂面,最夸张的一次,一天时间,下了十六回挂面。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阿城个人的巅峰,亦是文青群体登上时代潮头的具体表达。《棋王》发表两年之后,崔健唱响了《一无所有》,王朔陆续发表了《顽主》《动物凶猛》等小说,百花齐放的觉醒时代到来,文艺追求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潮流。马未都说,那个年代人们相亲谈的都不是房子车子,必须得聊文学,高晓松等华语乐坛早期的流行音乐人,也是在那个年代蓄起长发,在校园中潇洒“茬琴”,仿佛找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
那是当之无愧的文青时代。
这份好景大概只持续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九十年代中期,商业化的大潮涌来,冲散了文艺青年的阅读与弹奏,以至于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副产品,就是文艺青年从时代中心不可遏制地走向了边缘。
我们从教育角度就可以看出端倪。最早关于教育的说法,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意思是只要有书念就比其他工作强,虽然这句话已然不符合今天的政治正确,但确实一度流行。然而后来,光读书不够了,指向更加明确,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社会发展的刚需,迫使普通人要学习有明确功用的一技之长,文艺青年的纸上谈兵和伤春悲秋,既不利于国家建设,也不利于个人经济状况的改善。
经历过文理分科的八零九零后们一定不陌生,那些班级里最聪明的头脑,都以能取得更高的理科成绩为荣,文理两科,看上去是平等的两个选项,而实际上,文科只是理科的备胎,大多数选择文科的人,都不是因为真心热爱文科,而是没能力学习理科。
从最受欢迎到最受歧视,文艺青年度过了过山车式的一段岁月,然而,一个私人观察出来的好消息是,我认为以上所述的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新文青时代的见证者。
2
“新文青时代”的到来,是以一些人的成就为信号的。
如果让我评选2017年最出人意料的红人,我会选择许知远。像他这样严肃、拧巴、完全不会讨好人、长相也不讨喜的知识分子,通常只适合出现在高校中,做一小撮人的学术偶像,可是,他在去年屡登热搜成为话题人物。
介入许知远和他所讨论的问题是有门槛的,他和陈鲁豫式的访谈者正好相反,他从不谈论具体的问题,永远不会问“你吃了没”或是“你今年赚了多少钱”,他关心人面对大时代的反应,顺应、戏谑、调笑还是焦虑,也关心每个人的个人哲学。事实上,这类话题是精英而小众的,愿意思考和有能力理解这类问题的人都是少数。可是从数据上看,《十三邀》第二季的总播放量轻松过亿,仅一个新春合集,播放量就高达7423万,而他在蜻蜓FM的付费音频《艳遇图书馆》也轻松突破了500万的播放量。
无独有偶。在许知远的另一个维度是梁文道,他从2015年6月开始做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到2017年7月,两年时间里做了197期,总播放量为4.6亿,平均每期节目都有200万以上的播放量,虽然和大体量的网络节目无法相比,但也算是文青内容创业中的一份硕果。而同为梁文道出品、由窦文涛主持的文青谈话节目《圆桌派》,平均每季播放量都已过亿。
从许知远到梁文道,他们的内容产品的成功,证明有深度思辨意愿的年轻群体,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得多。推而广之,既然并不擅长与社会大众打交道的许知远和梁文道都能在“新文青时代”取得小成,那么像高晓松这样在网络文化中穿梭有余的文青,取得大成就并不奇怪了。
高晓松的《晓说》《晓松奇谈》累计产生了多少播放量,已经不必具体统计,因为这一定是个几十亿级别的天文数字。
单说最近,他在蜻蜓FM开设的音频节目《矮大紧指北》,上线一个月购买人数就超过十万人。在新节目中,高晓松化身为自己的反面“矮大紧”,说起了关于父母离异、大年三十找前女友等“高晓松”不方便说的话题。2月22日晚上,高晓松还送上了自己首次的音频直播作为付费会员的Bonus,在新年假期结束的第一天与网友连麦。
在昨天晚上高晓松的首次音频直播中,一个关于文青的中年危机讨论令人印象深刻。有听众现场问高晓松如何看待中年危机,高晓松回答,最新的说法是45岁之前都是青年,时代的速度和健康的饮食,让每个人延长了很多生命,所以他也才刚刚步入中年。而所谓的中年危机,也并不可惧,就如同年轻人总被爱情一叶障目一样,中年人也会认为这个危机是人生的终极难题,其实,只要保持躁动,度过这个阶段,人都会有豁然开朗之感,“我没有见到一个人中年危机一直到70岁的”。
而说起高晓松,他总是那个能摸到时代脉搏的人。80年代文青最受欢迎的年代,他苦练吉他做音乐;90年代商业社会大潮来临,他与宋柯合作创立麦田音乐;进入21世纪,互联网异军突起,他的足迹从搜狐到新浪,又到如今的阿里;在一个新的文青时代到来的时候,他用视频音频等各种媒介传递自我,凭一己之力,将“诗与远方”设定成了一种文青生活范式。
无论你是否认可“诗与远方”,事实上,当这样的词汇像病毒营销一样在一个社会中传播扩散开来,已经说明它绝对切中了某种不被抒发的集体情绪,在此之前,人们只是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准确的词汇来总结归类而已。
3
关于“新文青时代”出现的原因,我认为可以从经济角度寻找答案。
如果把世界理解为一个班级,中国应该是班里最出挑的偏科生。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狂奔式的发展,它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和国际影响力无须赘述,是这个班级里最大的变量。然而,中国的发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集中放大,我们在追求GDP的同时,一度枉顾精神层面的需求,富起来的中国人破坏了一切的旧信仰与旧价值,但新的信仰和新的价值,还远没有被建立。
这或许才是“新文青时代”得以存在的真正原因。在经济发展进入到平台期的时候,中国人意识到,该把木桶里最短的板接上了,所以“新文青时代”或许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度过了极速狂奔阶段,进入了修缮与调整的新阶段。
和80年代的“旧文青时代”不同,“新文青时代”有属于它自己的新状况。
首先,是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别。1982年,中国的中小学入学率仅为55.17%,而美国在1974年这一数据就达到85%,日本更是达到惊人的98%。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导致当时的国人很难接受复杂的文艺形式,无论是阿城王朔的小说,还是崔健的歌词,语言都简单直白,虽有隐喻,但无法传递更深度的思考,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
如今的情况不一样。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报告,每十万中国人中,就有12445人受过大学教育。所以哪怕是相对晦涩的许知远和梁文道,也可以拥有广泛的观众,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国有着广泛的受教育群体,年轻人不仅有进行深度思辨的意愿,同时,他们也具备相应的能力。
这是所谓“新文青时代”得以成立的一个底座。
其实,若是和今时今日具有等量声名的人物相对比,大家都会发现,当年阿城出名后所获得的回报实在是少得可怜,无外乎是让各大文学刊物注意到他,向他约稿,付些稿费罢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换成了茶叶和挂面。在阿城名声大噪的时代,他接受记者采访,提到靠《棋王》其实养活不了自己。王朔的发行量可以养活他,但阿城不行,作家和畅销作家是不一样的,“畅销作家是有钱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饭的概念”。
在文青与利益的关系上,“新文青时代”更完备。在旧文青时代,再出名的文青和钱之间,也隔着万水千山,而今时今日,高晓松在蜻蜓FM的《矮大紧指北》一个月就可以创造2000万元的销售成绩,而付费会员还认为,从高晓松这里得到了这么多年的免费知识,在这里给他补上是一种偿还。这种多赢局面,在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当下的内容消费产品,还是和文理分科类似,一派讲价值,一派讲功用。许知远、梁文道和高晓松这些赫赫有名的大文青,都属于前者,他们树立典范,输出的是思考方式;而另一派则如《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蔡康永的情商课》,讲究学以致用。
因为这两派的存在,提供知识服务的平台也不得不做取舍站队,比如蜻蜓FM站队“价值派”,汇集了高晓松、许知远、蒋勋、老梁、方文山等老牌文青,主打文艺属性和陪伴功能;而如喜马拉雅和得到App,则更偏“功用派”,核心产品是马东的《好好说话》和《李翔商业内参》,主打实用属性和教育功能。
说白了,“功用派”是要建立一所学校,而“价值派”则是上学时偷偷翻看的金庸全集,前者在课桌上面,后者在课桌里面,你说两派哪个重要?答案当然是都重要。不过若非要区分,我以为,不是每个学生都能看得进去课本,但几乎没有学生不爱看金庸。
4
在文艺青年最受歧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当道之时,梁文道一度感慨,“文艺的人要装俗才能获得社会认同”,有些人明明就是发自内心喜欢中国古代字画,但却必须要装出另外一副样子,时不时还得讲讲荤段子调节气氛,实在是太可悲了。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大家可以不再装了,喜欢自己喜欢的事物,并不丢人。
诚如前文所言,“新文青时代”是经济发展进入平台期之后,偏科的中国人进行的一次集中补课。我们需要新的信仰,新的价值,这势必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最为关键的是,它们的答案必是多元的,我们会有要成为下一个马云的野心家,也会有得过且过的佛系青年,许知远有他的观众,高晓松也有他的听众,百花齐放的年代,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坐标。
套用马克思最广为使用的那句名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全新的理解方式或许正是说,有钱之后,想往脑子里装些什么,你可以自己说了算。据《2017中国互联网消费生态大数据报告》显示,目前的消费者更愿意为高级的精神产品买单。
如此想来,这一浩浩荡荡的“新文青时代”,应该是多年艰苦卓绝的经济建设之后,时代给予中国人的一份礼物。
所以,上前来,挑一份你想要的礼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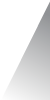
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