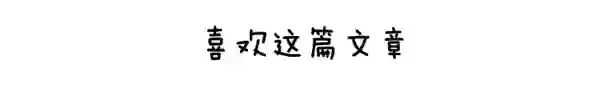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丨走近吐蕃文明
2017年9月28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内一片喜庆景象,每五年一度颁奖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全国人大副主任委员马凯等出席盛会并为获奖者颁发奖状与证书。
我社作者四川大学霍巍教授所著《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科学出版社)荣奖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据吴玉章基金会及吴玉章奖组委会介绍:“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面向全国,主要奖励国内有重大影响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论著,旨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自1987年至今,该奖已颁发六届,郭沫若、吕淑湘、胡华、金冲及、胡绳、王力、王钟翰等一批著名哲学社会科学家先后荣获该奖项,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已成为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较高规格的奖励。”
据悉,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吴玉章基金委员会为表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有卓越贡献的学者设立的专门奖项,于2012年首次颁发,每人奖金100万元,被认为是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齐名的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最高荣誉。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每5年评选一次。现评奖学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教育学、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8个学科。郭沫若、吕叔湘等一批著名社会科学家先后荣获该奖项。
颁奖典礼开始前,吴玉章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01岁的宋平同志,宋平同志夫人、101岁的陈舜瑶同志,吴玉章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102岁的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袁宝华亲临人民大学看望各位获奖代表,吴玉章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前总理、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同志专程发来贺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玉章基金委员会主任马凯为获奖者颁奖并讲话。教育部副部长孙尧、社会科学司副司长谭方正,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张淼,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崔新建,著名人口学家邬沧萍、著名哲学家陈先达、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著名经济学家吴易风、著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家高放,以及兄弟院校代表出席典礼,共同见证这一时刻。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校长刘伟,原校长黄达,原党委书记马绍孟、程天权,党委常务副书记张建明,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吴付来,副校长洪大用、贺耀敏、吴晓球,党委副书记郑水泉,副校长刘元春、杜鹏出席典礼。中国人民大学各院系、部处负责人,部分学院师生代表,以及新闻媒体代表参加典礼。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举行。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霍巍教授走近神秘的吐蕃文明吧。
霍巍生于成都,祖籍河北,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担任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09年 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并受到总书记、总理亲切接见。
《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对吐蕃考古新发现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对其中吐蕃墓葬、出土棺板画、金银器、马具、丝绸、各地佛教考古遗存、祭祀遗迹、大石遗迹、城堡居室遗址等主要的考古发现结合文献材料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对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出土资料所反映出的吐蕃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等问题也做了研究论述。《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适合于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史、藏学等领域研究者以及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以上、对西藏文化有兴趣者阅读。
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
关于“吐蕃文明”的学术界定
为了便于研究工作的展开,这里首先有必要对本文所称的“吐蕃文明”一词加以适当的界定。对所谓“文明”这一概念,近年来学术界讨论较为热烈,对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它既可以因时代与地域或民族的差别而不同,也可以因人们对其的理解而不同。有时,它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所谓“野蛮”相对而言;有时“文明”则又作为“文化”的另一种别称。而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文明”这一概念,是指与史前社会有别的古代文明社会。具体到吐蕃而言,则是指吐蕃王国成立之后,吐蕃进入到西藏古代文明社会的这一时空范围内的文化面貌,其中当然也包括部分吐蕃王国成立以前有关吐蕃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的内容。
过去学术界在讨论“文明”及“文明起源”这一问题时,时常还会涉及另一个相关的概念,即所谓“文明标志”,国内外较为流行观点是将铜器、文字、城市等作为文明的标志或要素来加以讨论,以探索“文明起源”的问题。对于这种流行的观点,已经有学者提出过不同意见:“这种文明观明显地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是这类‘标志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难适应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其二是它将文明看成是单项因素的凑合,形成所谓‘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这既难以对文明社会的出现作出结构特征性的说明,更难以对文明社会形成过程作出应有的解释。”但在目前情况下,如果要以某些客观标志物作为文明起源的客观标准,就很难避免这种开列清单的做法。
在本文中将不会主要讨论关于吐蕃文明的起源问题,笔者的关注点和重点将主要放在吐蕃文明已经形成的吐蕃王国时期,而对尚未进入文明社会的西藏史前时期仅仅作为讨论时的参照,因此,将会自然地回避所谓“文明起源标志”问题的讨论,而将笔墨主要放在对吐蕃文明形成之后、作为成熟形态的吐蕃文明进行若干专题研究。那么,本文所称的“文明”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从属于“文化”这一概念之下的第二层次概念。
在本文中,“文化”这一概念较之“文明”这一概念内涵要更为宽泛,按照目前海外学术界较新近的观点,有意见将“文化”大致划分为三个层次的内容,即:第一层次,精神文化,其中又包括知识类(如语言、对世界和各类事物的认识、认识类哲学、科学理论、方法论、各类技术、管理学等)和信仰、价值、规范和素质类(如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进取价值、伦理价值、法律体系、人格观念、民族性等);第二层次,过程性文化,如生活方式、运作制度等;第三层次,结果性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食品、器物、建筑和一切其他类型的人造之物。本文的研究特点是根据考古材料来研究吐蕃时期的文明成就,由于考古材料本身的特点是以实物形态反映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就研究对象和所使用材料的特点而言,主要涉及的内容与前文所列有关“文化”的第三层次———结果性文化最为贴近。当然,透过这些结果性文化的物化形式,同样也可以反映出第一、第二层次(即精神文化、过程性文化)文化当中的若干问题。本文对吐蕃所作的专题研究之所以多采用“文明”这一概念,也主要是基于除了文献材料之外,目前唯一能够说明吐蕃时期文化面貌与文明状况的,只能够是它的物质遗存———即古代人们活动和环境所遗留下来的遗物与遗迹这一现状来考虑的(在考古学上,将这些物质文化遗存有的命名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从这个意义而言,本文的“吐蕃文明”这一概念,既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考古学的概念。
吐蕃考古与吐蕃史研究
以往对于吐蕃文明的研究,通常都是涵盖于吐蕃史研究的领域。而吐蕃史的研究自从敦煌藏经洞大量吐蕃时期古藏文写卷历史文书以及新疆等地的古藏文简牍发现以来,首先在西方学术界引起高度重视,成为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迄今已经形成长期的研究传统,在海内外涌现出一批知名学者,有大量高水平的论著问世,对此笔者不拟赘述。如同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一样,自从考古学诞生之后,便与历史学共同承担起复原历史和解释文明发生、发展的任务,而吐蕃考古与吐蕃史之间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着共同的研究目的,但又有不同的侧重点和方法论。概括而言,吐蕃史主要关注的重点是依据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传世的以及地下出土的文献材料)研究解释吐蕃历史发展的基本线条、与吐蕃史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吐蕃社会制度的发展演变等,从中总结研究吐蕃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以往的吐蕃史研究中,对于吐蕃文明的具体层面(如上文中提及的艺术、食品、器物、建筑、手工业及其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生存模式、交通与贸易等)则往往关注较少。而吐蕃考古却可以与吐蕃史研究形成各自的优势互补,一方面,通过地面的考古调查和地下的考古发掘,考古学能够为吐蕃史研究不断提供新的文献资料(如吐蕃碑铭、简牍、铜器铭文等);另一方面,由于考古学的学科特性,对于当时人们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各类遗迹与遗物都会有所关注,自然就会提供许多文献资料缺载的社会生活内容甚至其中的细节。如果说我们将吐蕃史研究比喻为如同人体的骨架和经脉,那么吐蕃考古则好比是人体的血和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丰满而生动鲜活的形象。
葛兆光先生在他撰写的枟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枠第一卷中,对于过去思想史的写作有如下的评述:“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和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这里,笔者尤其有感于葛兆光先生所提到的“普通的社会生活”以及“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这在以往的吐蕃史研究中,也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在伟大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重重光环笼罩之下,吐蕃人“普通的社会生活”状态以及与精英权贵所不同的“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等层面的问题常常很难有人加以关注。本文使用的“吐蕃文明”这个概念,都将可能涉及这些过去在吐蕃史研究中存在明显不足或者相对薄弱之处,而吐蕃考古研究的开展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不足,使吐蕃史研究得到深化和提高。
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最大的不同点,是前者主要根据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等理论方法,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作为研究对象;而历史学则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史料学、史学理论等)依据传世的文献材料开展研究,但是在研究目标上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都是为了复原与阐释古代社会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自从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提倡以地下发掘之材料与地上的文献材料两者互证以研究历史的“两重证据法”以来,在学术研究方法上运用这种方法也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地下出土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学者们所认识和肯定。在吐蕃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如前所述,正是由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古藏文历史文书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简牍的解读与研究,才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吐蕃史研究发展成为今天的强大研究阵容,追溯东西方藏学研究发展的历程,也不能不提到在敦煌和新疆等地这些吐蕃文献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一个多世纪之后,当西藏的文物考古事业不断发展,有关吐蕃社会历史的考古材料有了更多积累的时候,我们更应当强调和倡导运用地下考古资料、结合文献材料来加强和充实吐蕃史的研究,这一点我想现在已经不会有人提出怀疑。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与传统的吐蕃史研究相比较,吐蕃考古起步很晚,基础资料的积累十分薄弱,考古材料较为零散,在目前阶段与吐蕃史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论及),这就更是需要从事吐蕃考古的研究者充分利用吐蕃史丰厚的积淀与取得的研究成果,学习其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视野,奋勇追赶,才有可能做出一定成绩。
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阐明本文的宗旨和特点了: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之处在于,本文是一部以考古学的方法、理论为基础,利用考古资料来研究吐蕃社会文明发展状况的学术著作,笔者力图将吐蕃帝国放置于一个广阔的学术视野当中来加以考察,通过对不同类型的考古材料进行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结合汉、藏文献材料和现今吐蕃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对考古材料本体特征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吐蕃人的社会生活与一般知识、信仰、工艺等文明成果进行分析探讨,并观察其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广泛联系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
那么,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探讨吐蕃文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特点,可以预期取得哪些新的突破呢?
首先,考古资料与文献材料相比较,它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可以超越传统历史文献当中的各种主观因素。我们知道,在吐蕃王朝以前,吐蕃没有成熟的文字和历史文献记载,吐蕃王朝以前的历史缺乏可靠的历史年表,即使在吐蕃王朝创立藏文字之后,保存至今的真正属于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记载也相当贫乏,除敦煌出土的吐蕃历史文书,新疆、青海等地发现的一些藏文简牍和西藏本土现存的部分金石铭刻之外,传世的藏文历史著作成书年代多在14世纪之后,所以在更多的情况下还需要依靠唐代汉文文献来研究吐蕃历史和吐蕃文明。而出于不同的修史目的,这些文献记载要么充满神秘的宗教色彩,难以直接成为可靠的历史资料;要么带有明显的民族偏见和“中原正统观”色彩,必须加以修正。加之无论是在汉、藏历史文献当中,都比较偏重于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宗教发展等“大历史”方面的描述,要从中梳理出有关吐蕃时期人们衣、食、住、行、工艺传承以及宗教活动中的具体细节(如仪式过程、使用法器、祭祀场所的营建)等“小历史”方面的记载,却无疑是“沙海沥金”。而考古材料则可以为我们提供直观可靠的实物,来弥补上述这些文献记载的不足,呈现给人们以客观、真实的文明样态。
其次,考古材料还具有具象性的特点,发掘出土的考古材料犹如给我们提供了观察一个时代的不同切片,虽然它难免带有考古材料常见的不可避免的分散、零碎等缺陷,但对于认识一个社会古代文明的各个方面和不同层次,却恰恰又是它的长处之所在。我们在后面本文各章节的不同专题研究中,将会看到考古学将会提供给我们多么丰富的素材:从吐蕃王陵的营建,到一般平民的丧葬活动;从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建筑,到一个普通百姓的村落遗址;从制作精美的金银器皿,到朴素无华的民间器用;从厚重华丽的西方织锦,到淡雅素净的东方丝绸;从剽悍威武的吐蕃马具,到平和恬静的佛教遗珍……正是这些考古发现,可以为我们勾勒出吐蕃文明的一些基本面貌,从中体现吐蕃文明的地域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
再次,考古材料总是能够“推陈出新”,不断刺激和更新传统观念。还可以预期的是,地下考古材料的发现总是会带给我们一些文献材料所不能预设的新问题,刷新过去在吐蕃文明史观上的一些传统认识,启发我们的思维,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本文摘编自霍巍著《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序论,内容有删减。
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
霍巍 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32542-6
《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对近年来吐蕃考古新发现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对其中吐蕃墓葬、出土棺板画、金银器、马具、丝绸、各地佛教考古遗存、祭祀遗迹、大石遗迹、城堡居室遗址等主要的考古发现结合文献材料进行了专题研究, 并对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出土资料所反映出的吐蕃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等问题也做了研究论述。
(本期编辑:安 静)
一起阅读科学!
科学出版社│微信ID:sciencepress-cspm
专业品质 学术价值
原创好读 科学品味